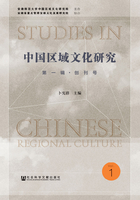
从汉代风俗观念看国家治理与区域文化的发展
彭卫
区域文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既包含着特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精神世界的表现,也包含着在这一精神的支配下人们的创造,从而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风俗民情是在自然和人文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风俗民情具有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意义。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群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并对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风俗民情便成为该区域文化的核心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个地区区域文化的思考,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地区风俗民情各种表现的认识。
与今天的“风俗”概念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风俗”有两层意义。其一,定位于政治性和文化性含义的风俗,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有“周末风俗”、“两汉风俗”和“宋世风俗”条,所论内容是这三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气象和风尚。其二,定位于风土人情,即风俗的范围和内容包括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式,以及性格和精神面貌的风俗,如班固所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这种大“风俗”概念,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它所包含的大量的历史信息,体现了历史上区域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也有理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经验和借鉴。下面我们以汉代为例略作说明。
笔者曾指出,汉代风俗观念集中于五个方面。(1)风俗是一种差异,而这种差异源自不同的自然和文化背景,是为风俗观中的环境影响说。(2)上古时期风俗淳厚质朴,后世风俗浇薄败坏,是为风俗观中的厚古薄今说。(3)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带来风俗的沦丧,是为风俗观中的财富与风俗背离说。(4)大一统的王朝需要统一的风俗,统治者应致力于风俗的一致化,消弭差异有助于保证国家稳定;相反,风俗的多样化则必然瓦解统治基础。是为风俗观中的“齐同”说。(5)良好的风俗要依靠社会上层尤其是君主或圣人的努力来建立,是为风俗观中的圣人施教说。[2]这五个方面大都与国家治理有关,其思想萌芽在春秋以来的百家争鸣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风俗观念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得到全面展开,并显示出明显的思维同一性,即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着上述这些观点。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观点的许多痕迹,就此而言,汉代风俗观念的上述表达,具有里程碑和导向性的意义。
何以汉代政论家和学者将风俗与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在于,风俗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社会表现,它通过信仰、习俗将单个的个体连接成彼此联系的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群体;而国家则是通过权力进行控制的最高组织,它通过行政管理、法律等制度化的内容,使社会得以运转。这是两种立足不同、方式不同、内容不同的力量,而它们的相同之处则是,人群的生存、社会的发展不能离开一个有效率的、公正和廉洁的政府,也不能离开养育着不同地区人群生存的文化土壤。因此,将民间和地方风俗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顺理成章地成为汉代人思考的基本内容。
实施风俗一体化的“齐同”说的提出和实践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在商、周(西周和春秋时期)王制社会,否认不同地区的风俗存在的合理性的声音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诗经》十五“国风”显示了人们对各地风俗差异的认可。这种情状与当时的“封建”制度密切相关:受到商王和周王分封的方国和诸侯国保持着自己的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也就使得它们所控制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保有自己的合法性。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
大一统的政治和军事表现从战国时逐渐成为一个历史趋势。而在思想文化方面,齐同风俗成为构建大一统理论的一个要点。战国后期儒家代表性人物荀子指出:“风俗以一”是“政令以定”结果,如果“有离俗不顺其上”,就会导致“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的恶果。[3]汉代思想家和政论家大抵以荀子之说为依归,并在大一统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发展了“齐同”观。其基本点是“《春秋》所以大一同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的结果是“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4]这即是说,统治者应致力于风俗的一致性,取消风俗的区域差异有助于保证国家稳定,而风俗的多样化则必然瓦解统治基础。平帝时,王莽遣风俗使者分行郡国览观风俗,以证“天下风俗齐同”,[5]显示了国家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努力。
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是经历了漫长过程而形成的,它的存在显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体现了它是区域文化中无可替代的力量。其实,战国以来风俗观中的环境影响说已经触摸到了这一点。《吕氏春秋·用众》指出:“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6]《淮南子·地形训》和应劭《风俗通义·序》认为,自然环境和食物摄取与不同地区人群的性格和品质具有因果关系,所谓“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7]、“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8]。贾谊则强调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生而同声,耆欲不异”,但在其成长过程中,因“教习”的不同形成风俗差异。[9]这些表述从自然论和人文论的角度说明“齐同”缺乏必要的立论前提,即没有解释何以各地风俗民情可以摆脱各自所处环境的影响,而成为统一的模版,因而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觉。
汉代历史的实践同样证明,王莽等人的“齐同”实践不过是编饰出的谎言,“齐同”主张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虚幻。王莽之前的司马迁和依附了王莽的扬雄在《史记·货殖列传》和《方言》中使用的区域分布标准不是汉代的行政建制,而是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区域空间——这个空间的许多分野就是《诗经》十五“国风”。在王莽之后的班固同样使用的是司马迁、扬雄模式。他们的描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诸国风俗在汉代依然稳固地存在着,从而显示了一个时代风俗与国体和国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重合的复杂关系,显示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差别,显示了一个时代的风俗习尚在“变”与“不变”中纠葛和合流,也显示了保留了区域文化的汉帝国文化景观是那样的绚烂多彩。在汉代和汉代以后的历朝各代,还没有发现因区域文化的保存和蓬勃发展而导致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变乱。这些历史提示我们:要尊重包含风俗习尚在内的区域文化的特点;要承认在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多元文化的存在不是国家的离心力量,而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因此就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将风俗整齐划一。
在以往风俗史的研究中,人们似乎忽略了司马迁的一个重要主张。在《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他即写下了对从先秦至西汉前期长时段的不同地区经济和风俗民情总趋向的评论,写下了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情状的主张:“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0]与其父相同,司马迁思想中有着浓厚的黄老因素,因此“因之”等等的出现不足为奇。但值得注意司马迁的判断,是通过他对历史的观察而获得的,借用今天的话说,是论从史出而非以论代史。他承认不同地区文化差异存在的合理性,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活动和风俗民情,提出绝对的“善”与“恶”、“好”与“坏”是不存在的,从而展现了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历史纵深感和思想的厚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司马迁的这段话提倡让人性自由地表现和发展,反对压抑人性,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最深刻理解。[11]
一个地区的风俗习尚是否会出现变化?国家是否就是简单地“因袭”这种风俗而不会有所变化?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没有明确指明此点。不过,从司马迁所秉持的历史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如“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12]等)和历史上的人是有作为的而非消极的基本历史观念来看,尽管司马迁强调的是对于一个地区有着长期历史传承的风俗习尚,当政者应当慎重行事。这从逻辑上应当能延伸出一个地区的风俗不是凝固不变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应当与时俱进有所作为的结论。司马迁的一些认识虽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但在区域文化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上,“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正是先贤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研究》主编)
[1]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第1640页。
[2] 彭卫、杨振红:《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3]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中华书局,1988,第286页。
[4] 《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3页。
[5]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359页;《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4071页。
[6]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四,学林出版社,1984,第232页。
[7]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451页。
[8] 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1页。
[9]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52页。
[10]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4,第3949页。
[11]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38页。
[12] 《史记·平准书》,第1714、1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