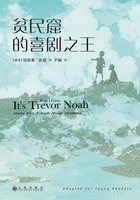
第4章 天生有罪
我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长大,情况有点令人尴尬,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混合种族家庭,而我自己正是那个混血儿。我妈妈帕特丽夏·努拜因赛罗·诺亚是黑人。我爸爸罗伯特是白人。准确地说是瑞士裔德国人。种族隔离期间,最严重的一种罪行就是与另一个种族的人发生性关系。显而易见,我爸妈就犯了这种罪。
在任何一个建立在制度化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种族融合不仅仅是在挑战这一体制的不公,还揭示了它无法持续发展和不合逻辑的本质。种族融合证明不同种族之间可以相互融合,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种族的人想要彼此融合。因为混血儿代表了对这种体制逻辑的谴责,种族融合于是成为比叛国更严重的罪行。
第一批荷兰人的船抵达塔布尔湾九个月后,南非就诞生了第一批混血儿。就像在美洲一样,这里的殖民者也知道怎么勾引当地女人,殖民者们常常这么干。但与在美洲只要任何人的身体里混进了一滴黑人的血就自动归为黑人不同,在南非,混血人既不属于黑人,也不属于白人,他们自成一族,被称为“有色人种”。政府强迫有色人种、黑人、白人和印度人登记各自的种族信息。根据这些分类,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重新安家落户。印度人聚居地与有色人种聚居地相互隔离,有色人种聚居地又与黑人聚居地相互隔离,而这些聚居地又都与白人聚居地相互隔离,不同聚居地之间都隔着一片空旷的缓冲地带。法律严禁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后来又修订了相关法规,变成禁止白人和所有非白人之间发生性关系。
政府费尽心机想要执行这些新法规。违反这些法规的人会被判处5年监禁。如果一对跨种族夫妻不幸被捕,那就只有祈求上帝怜悯了。警察会踹开他们的家门,把夫妻俩拖出来,一顿毒打之后再逮捕他们。他们至少会这么对待牵涉其中的黑人。
如果你问我妈妈,是否考虑过在种族隔离时期生下一个混血儿的后果,她会回答:没有。她身上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你必须先拥有这种精神,才能像她那样去做一些事情。如果你稍微迟疑考虑一下后果,就永远无法做任何事。虽然如此,生一个混血儿仍然是不顾后果的疯狂行为。一直以来,为了在夹缝中生存,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出丝毫差错。
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男性一般在农场、工厂或矿场工作。黑人女性则是做女工或女佣。这差不多就是黑人所能有的选择。我妈妈不想在工厂上班。她还是个糟糕的厨师,绝不会容忍某个白人女士整天对她指手画脚。因此,她遵循本性,找到了一个本不属于她的选项:她参加了一个秘书培训课程,学习打字。当时,黑人女性学习打字就相当于盲人学开车。这份努力令人钦佩,但可能根本没人会雇你干活。法律规定,白领工作和技术型工作都是留给白人的。黑人不能在办公室工作。然而,我妈妈是个反叛者,而幸运的是,她的反叛恰逢其时。
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抗议,南非政府开始进行一些小改革。其中就包括象征性地雇佣黑人从事低级白领工作,比如打字员的工作。我妈妈通过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秘书工作,这是一家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布拉姆弗泰恩的跨国制药公司。
我妈妈开始工作时,还是跟我外婆一起住在索韦托,几十年前,政府把我们一家重新安置到这个小镇。但我妈妈在家过得并不开心,她22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住到了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这么做只有一个问题:黑人住在那里是违法的。
种族隔离的终极目标是让南非成为一个白人国家,所有黑人都被剥夺公民身份,并被重新安置在黑人家园“班图斯坦”,它们是半自治的黑人领土,但实际上就是位于比勒陀利亚的政府的傀儡。但这个所谓的白人国家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黑人劳动力的奉献,这就意味着必须允许黑人生活在白人聚居地附近的小镇上,而这些小镇其实就是政府为黑人劳工修建的贫民窟,索韦托就是这样的郊外小镇。小镇是你生活的地方,但你只能凭借劳工身份留在那里。如果哪天你失去了这一身份,就会被赶回黑人家园。
想要离开郊外小镇去城里工作,或是因为其他原因要进城,你必须带上一张标有你身份证号码的通行证,否则,你可能会被逮捕。与此同时还有宵禁令:过了某个特定时间,黑人必须回到小镇,不然就有被逮捕的风险。可我妈妈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她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家。于是她留在城里,晚上就躲在公共厕所睡觉,后来她从设法留在城里的其他黑人女性那里学会了一套城市生活法则。
这些黑人女性中有很多是科萨人。她们跟我妈妈说一样的话,告诉她如何生存下去。她们教她如何穿着女佣的行头在城里来去自如。她们还把愿意在城里出租公寓给她的白人男性介绍给她。这些男人大多是外国人,比如一些不在乎相关法律规定的德国人和葡萄牙人。幸好我妈妈有工作,可以支付房租。她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一个德国男人,他愿意以他的名义给她租一间公寓。她搬了进去,还买了一堆女佣服穿。她被逮捕过很多次,有时是因为下班回家的时候没带身份证件,有时是因为过了规定时间还待在白人聚居区。违反通行法的处罚是在监狱里待30天或交50兰特罚金,这笔罚金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她会东拼西凑地凑齐这笔罚金,交完钱后就没事人一样去做自己的事。
我妈妈的秘密公寓在一个叫希尔布罗的社区。她住在203号。同一条走廊上住着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棕色眼睛的瑞士裔德国侨民,他的名字是罗伯特。他住在206号。作为曾经的贸易殖民地,南非一直有大量侨民。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大批德国人。大量荷兰人。希尔布罗当时就是南非的格林威治。那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既具有国际化风情,又充满自由气息。那里有许多画廊和地下剧场,艺术家和演员敢于在各个种族的人群面前大声疾呼,批评政府。那里还有许多餐馆和俱乐部,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开的,服务各色人等,包括讨厌现状的黑人和认为现状很荒谬的白人。这些人还会举行秘密集会,集会地点通常是在某人的公寓或是被改造成夜店的空地下室。从本质上讲,融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集会本身并不带有政治性。人们就是聚在一起,结伴取乐,开开派对。
我妈妈也融入了这样的生活。她总是去参加聚会、派对,跳跳舞,见朋友。她是希尔布罗塔的常客,那座塔是当时非洲最高建筑之一。顶层有一家带旋转舞池的夜店。那是一段欢乐时光,但同时也危险重重。那些餐馆和俱乐部不时被关停。有时候演员和顾客还会被逮捕。这就像玩掷骰子一样。我妈妈从来不知道该信任谁,谁会向警察告发她。邻里之间都会相互告发。
独自在城市生活,既不被人信任,也不能相信他人,我妈妈开始越来越多地跟她觉得安全的人待在一起:住走廊另一头206号的高个瑞士裔男人。他当时46岁。她只有24岁。他沉默寡言,她活泼外向。她会在他的公寓门前停下来聊几句。他们一起去参加地下集会,去有旋转舞池的夜店跳舞。两人自然而然地擦出了火花。
而法律禁止这个男人与我妈妈组建家庭也成为某种吸引力。她想要个孩子,却又不想有个男人来干预她的生活。而我爸爸嘛,据我所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生孩子表示拒绝。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了。
在他表示同意之后,过了9个月,也就是1984年2月20日,我妈妈住进了希尔布罗医院,按计划接受剖宫产。与自己的家庭关系疏离,怀上一个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的男人的孩子,她就这样孑然一身。医生把她推进产房,剖开她的肚子,伸手进去取出一个黑白混血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出生违反了无数法律、法规和条例——我天生有罪。
医生把我取出来的时候还遭遇了尴尬一刻,他们当时说了句:“哈,这个孩子的肤色真是浅啊。”他们快速扫视了一下产房,没发现谁像孩子的爸爸。
“孩子的爸爸是谁?”他们问道。
“他爸爸来自斯威士兰。”我妈妈把答案引向了南非西部的这个内陆小国。
他们应该知道她在撒谎,却还是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说法。种族隔离时期,政府在你的出生证上标明一切:种族、民族、国籍。所有一切都要被归类。我妈妈撒了谎,说我出生在卡恩瓦尼,那里是生活在南非的斯威士人的半自治家园。因此,我的出生证上没有写我是科萨人,但其实我是。出生证上也没写我是瑞士人,政府不允许这么写。它只是标明我来自另一个国家。
我的出生证上没有爸爸的信息。从官方角度来说,他从来就不是我爸爸。我妈妈做好了独力抚养我的准备。她在朱伯特公园附近租了一间新公寓,那里紧挨着希尔布罗,她一出院就把我带到了那里。可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我爸爸就意识到,他不能看着儿子近在咫尺,却无法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们三个人在特殊政策下组成了所谓的家庭。我跟我妈妈一起生活。情况允许的时候,我们就会偷偷跑去见我爸爸。
大多数孩子是父母之间爱的证明,而我则是他们犯罪的证明。我只有在家里才能跟我爸爸待在一起。一旦出了门,他就必须跟我们隔着马路同行。我和妈妈以前经常去朱伯特公园。那就是约翰内斯堡的中央公园,里面有几个漂亮的花园,一个动物园,一个巨大的棋盘,上面摆着等人高的棋子,大家可以下着玩。有一次,妈妈告诉我,在我小时候,爸爸有一次试着跟我们一起散步。当时我们就在公园里,他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走着,我却追着他大叫:“爸爸!爸爸!爸爸!”公园里的人纷纷看过去。他吓得跑走了。我却以为他在跟我玩游戏,继续追上去。
我也不能跟我妈妈走在一起,一个浅肤色的孩子跟一个黑人女人走在一起,会招来太多非议。在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她可以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带去任何地方,但很快她就没法这么做了。我是个巨婴,一个巨大的孩子。我1岁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我已经2岁。我2岁的时候,你会以为我已经4岁。她没办法把我藏起来。
我妈妈还是找到了社会系统漏洞,就像她设法找到公寓和穿着女佣服一样。混血儿(父母一方是黑人,一方是白人)是违法的,但有色儿童(父母都是有色人种)却并不违法。于是,我妈妈就带着我以有色儿童的身份到处跑。她在一个有色人种聚居的地方找到了一家托儿所,她上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那里。我们公寓楼里住着一个叫奎恩的有色人种女人。我们想去公园的时候,我妈妈就会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去。奎恩会跟我并排走,表现得像我妈妈一样,而我妈妈则会在我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跟着,看起来就像是为有色人种女人干活的女佣。我有很多跟这个女人走在一起时拍的照片,她看起来跟我长得有点像,但其实并不是我妈妈。而站在我们身后看起来像是来抢镜的黑人女人才是我妈妈。没有有色人种女人陪伴的时候,妈妈会冒险带我出门。这种情况下,她会牵着我的手或抱着我,如果遇到警察,她就不得不把我放下来,假装我不是她的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已经有3年没有见过她的家人了,但她希望我认识他们,也想让他们认识我,于是离家出走的女儿回家了。我们住在城里,但假期的时候,妈妈通常会带我回索韦托跟外婆一起住几周。我对那个地方有很多回忆,一直觉得我们好像也同时在那里生活。
索韦托镇有近一百万人口,可以把它看成一座城市。镇上只有一出一进两条路。这样军队就能轻易把我们困在镇上,镇压任何叛乱。如果那群猴子发疯想要冲破牢笼,空军就会冲过来,把所有人炸得面目全非。从小到大,我从来不知道外婆一直生活在靶子中心。
在城市,虽然很难到处走动,但我们还是设法出门走动了。城市里有很多人外出走动,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种,大家来往于上下班路上,我们很容易混迹其中。可是索韦托只有黑人。像我这样的混血儿很难藏匿于人群,政府也盯得更紧。在白人聚居区你几乎看不到警察,就算看到了,也是那种平易近人的警察,穿着带领子的衬衫和熨得笔挺的裤子。在索韦托,警察随处可见。他们不穿带领子的衬衫。他们一身防暴行头。他们已经完全军事化。他们通常以小组形式行动,被称为“闪电特攻队”,因为他们会坐着装甲运兵车从天而降,我们称这种像坦克一样的车为“河马”,它装着巨大的轮子,车身上有可供射击的槽孔。你可不敢去惹“河马”。你见到它就得跑。这就是现实生活。我在外婆家里玩的时候,能听见枪声、尖叫声和向人群发射催泪弹的声音。
我对“河马”和“闪电特攻队”的记忆源于四五岁的时候,那时种族隔离制度终于开始崩溃。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警察,因为我们绝不能冒险让警察看到我。无论我什么时候去索韦托,外婆都不会让我出门。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是说:“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离开屋子。”我可以在屋子里玩,也可以在院子里玩,但就是不能去街上玩。而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都在街上玩。我的表兄弟和邻居家的孩子都会打开大门,出去四处疯玩,直到傍晚才回家。而我则只能苦苦哀求外婆让我出去玩。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能跟我的表兄弟们一起玩吗?”
“不行!他们会把你抓走!”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她说的是其他孩子会把我偷走,但其实她说的是警察。孩子会被抓走。已经有孩子被抓走过。肤色错误的孩子出现在错误的聚居区,政府就能介入,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把他扔进孤儿院。政府依靠“impimpis”网络来维护镇上的治安,所谓“impimpis”就是匿名告密者,他们会举报任何可疑活动。除此之外还有“黑杰克”,他们是为警察干活的黑人。外婆的邻居就是个“黑杰克”。每次她要把我偷偷带回家或带出门时,都要先确定他没有在监视。
外婆直到现在还在讲我3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受够了坐牢般的生活,于是在靠近车道的大门下面挖了个洞,钻出去跑了。所有人都吓坏了。大家组队出去找我。我并不知道我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危险。全家人都可能因此被驱逐出境,外婆可能被逮捕,妈妈也可能去坐牢,而我则可能被送去接收有色人种儿童的孤儿院。
于是,我被关在家里。除了公园散步的零星片段,我对于童年的回忆大多出现在室内,不是我和妈妈待在她的那间小公寓里,就是我一个人待在外婆家里。我没有任何朋友。除了我的表兄弟们,我不认识其他小孩。我不是孤独的小孩,我是擅长独处的小孩。我会看书,玩玩具,幻想出虚构的世界。我曾经活在我的想象中。我仍然活在我的想象中。直到今天,我也可以一个人待上好几个小时,非常开心地自娱自乐。我需要提醒自己应该跟其他人有所接触。
我当然不是种族隔离时期唯一一个黑白混血儿。今天当我在世界各地旅游时,总能遇见其他南非混血儿。我们的故事开始时都一样。我们的年纪也相仿。他们的父母通常是在希尔布罗或开普敦的某个地下派对相遇。他们也曾在违法公寓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后来几乎都离开了南非。他们的白人父亲或母亲经由莱索托或博茨瓦纳将其偷渡出境,这些“流放者”在英格兰、德国或瑞士长大成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种族隔离时期混血种族家庭的生活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曼德拉当选后,我们终于能过上自由生活。流放者们也开始返回南非。我17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个回归的流放者。他跟我说了他的故事,而我的反应则是:“等等,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离开?还有这么个选项?”想象一下你被人从飞机上扔了下去,你重重地跌落在地,所有骨头都断了,你去了医院,然后痊愈了,准备继续向前走,最后终于把所有一切都抛在脑后——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有个东西叫降落伞。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我径直回家,问我妈妈。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离开?我们为什么不去瑞士?”
“因为你不是瑞士人,”她答道,一如既往地固执,“这是我的祖国。我为什么要离开?”
***
在南非这片土地上,新旧交织,古老与现代融合,而南非的基督教就是绝佳的例证。我们从殖民者那里继承这一宗教,但为了以防万一,大多数人也保留了祖先流传的古老信仰。在南非,人们既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也相信巫术,施法和对敌人施咒。
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们生病了更愿意去找被轻蔑地称为巫医的萨满或传统治疗师,而不是去看西医。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们会因使用巫术遭到逮捕,并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我不是在说发生在18世纪的事情。我是在说5年前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个男人被指控用闪电袭击另一个人。闪电伤人的事情在黑人家园经常发生。那里没有高层建筑,也没有什么参天大树,人与天之间毫无遮挡,人们经常被闪电击中。当有人被闪电击中身亡,大家都认为这是有人利用自然力量发动的攻击。所以,如果你和那个被杀的人有过节,就会有人指控你谋杀,警察就会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