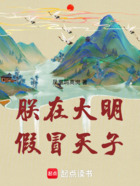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67章 累
张祁还记得自己刚穿越来的那一天,他孤零零跪在厅堂中央,青砖的寒意透过单薄的粗布麻衣渗入骨髓。
而于谦、张輗与张䡇三人高坐官帽椅上,集体垂眸审视着他,仿佛在打量一件待价而沽的货物。
可短短十数日过去,形势已然颠倒。
此刻他斜倚在锦绣堆叠的床榻上,身上裹着柔软的锦被,而于谦、张輗与张䡇三人却齐刷刷跪在榻前,额头触地,姿态恭敬。
这本该是最典型的“爽文”情节。
主角逆袭打脸,蝼蚁翻身做主,本该畅快淋漓,可为什么他只觉得……
累。
累极了。
张祁揉捏着太阳穴,思绪翻涌。
正如于谦先前所说,“午门血案”之后,满朝文武就相当于已经交出了一份无法反悔的投名状。
马顺是亲手杀害真郕王的刽子手,他的暴毙,等于斩断了这条最直接的证据链。
王振的倒台更是将文官集团与“假郕王”的政治利益牢牢绑定,那些查抄王振家产的,那些借机上位的,那些在清算中获益的,他们比谁都更需要维持这个“郕王”的真实性。
即便有人知晓真相,也绝无胆量揭穿张祁的真实身份。
因为质疑他的身份,就是在否定清算王振的合法性,是政治自杀,是自取灭亡。
正因如此,即便将来明英宗从瓦剌归来,即便孙太后或者于谦有意废黜他,也再不能以“冒充郕王”这个罪名发难了。
“张祁”这个身份,早已随着午门飞溅的鲜血一同消逝。
如今的他,从名分到血肉,从朝堂到宫闱,都已彻彻底底地蜕变成了朱祁钰。
那个死去的郕王,正借着他的躯壳,在权力与阴谋的浇灌下,重新活了过来。
因此当张䡇垂首奏报时,那日殉主的,便成了英国公府那个无足轻重的家奴张祁。
而活下来的,只能是郕王朱祁钰。
张祁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推演。
若是按照寻常网文的套路,此刻他早该以郕王之尊,将曾经折辱过他的张輗、张䡇兄弟踩在脚下,叫他们知道,昔日被他们讥讽为“英国公府一条狗”的人,如今是何等的权势滔天。
可现实终究不是网文。
北京城外的烽烟未散,瓦剌铁骑仍在虎视眈眈,土木堡一役已让勋贵折损大半,若此时再对英国公府下手,无异于自断臂膀。
更何况,石亨还未被他收服,羽翼未丰便贸然树敌,实非明智之举。
张輗、张䡇兄弟虽知他底细,但张辅之仇未报,眼下他们对明英宗和也先的恨意,终究远胜于对他这个“假郕王”的忌惮。
更重要的是,他尚未培植起真正效忠于自己的亲军。
故而现下这兄弟二人依旧是他最合适的护身符,至少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他们不得不护着他,也不得不与他同舟共济。
张祁放下揉按太阳穴的手,“既是殉主的忠仆,自当好生安葬。”
屋内三人俱是心头一震,这话里藏着的机锋,他们岂会不懂?
分明是要借“安葬家奴”之名,行掩埋真·郕王尸骨之实。
张䡇最先会意,沉声回道,“英国公战殁沙场,尸骨难寻,这家奴既以死相殉,不如就以国公朝服冠带入殓,令此奴随葬椁中,殿下以为如何?”
张祁暗自思忖,这般安排对朱祁钰而言倒也不算辱没。
史书记载,明英宗复辟后,不仅废黜了景泰帝的帝号,更将其降格以亲王礼草草葬于西山,使他成为永乐迁都后唯一一位未能入葬帝陵的大明皇帝。
虽然后来明宪宗又恢复了其帝号,并下令扩建陵寝规制,但始终未上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景泰帝才得以彻底平反。
如今朱祁钰得以入葬张辅墓室,倒是阴差阳错地保全了几分死后哀荣。
因为历史上张辅身后被追封为定兴王,其墓葬规制本就比照亲王礼制。
朱祁钰虽失帝位,却仍得以亲王之礼长眠地下,总好过历史上那般草草掩埋、凄凉收场。
张祁点了点头,“甚好,甚好,就这样去安排吧。”
他抬手虚扶,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都平身吧,本王病体初愈,见不得这般大礼,倒显得生分了。”
三人闻言,这才恭谨起身,衣袍窸窣间,各自归座。
张祁向后靠去,倚在床榻的锦缎靠枕上,他眉头微蹙,似在斟酌措辞,终是忍不住转向于谦,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王竑当廷出手殴打马顺一事,实非本王授意。”
“本王原只是想让张輗制住马顺,堵住他那张胡言乱语的嘴便是,谁曾想仪铭突然冲出来抱住本王,当时那场面,当真是始料未及。“
于谦捋须轻笑,目光深邃,“殿下不必自责,容下官为殿下说一段太祖皇帝旧事。”
“昔年元末天下大乱之时,韩山童借贾鲁治河之机,自称宋徽宗八世孙,与刘福通等人在颍州聚众起义,可惜事机不密,韩山童兵败身死。”
“其后,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年号‘龙凤’,建军‘红巾军’,而太祖皇帝因初投郭子兴帐下,亦奉龙凤为正朔。”
“彼时群雄并起,张士诚见风使舵,为避元军与方国珍夹击,不惜屈膝事元,竟受太尉之封,那陈友谅更是豺狼成性,先挟天完帝徐寿辉僭称汉王,尔后竟行弑逆之事,自立为帝。”
“唯有太祖高皇帝采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深谙韬光养晦之道,即便平定浙东,位极人臣,仍谨守臣节。”
“小明王虽晋太祖皇帝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太祖皇帝却始终以臣礼事之,不肯僭越半分。”
“反观张士诚,趁太祖皇帝与陈友谅鏖战之际,大肆扩张,北据徐州,南占绍兴,拥兵数十万,俨然一方霸主,其后竟遣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欲害小明王。”
“太祖皇帝不顾群臣反对,毅然亲率大军前去解围,虽救得小明王脱险,刘福通却战死沙场,此后小明王被太祖皇帝安置于滁州,仍奉为共主,太祖皇帝日日遣使问安,礼数周全。”
“而陈友谅此獠,趁太祖皇帝亲率主力北上解救小明王之际,竟率六十万水师直扑应天。”
“其军先围洪都府,幸有朱文正临危受命,死守孤城两月有余,终得太祖皇帝亲率二十万大军星夜驰援,陈友谅见势不妙,遂移师鄱阳湖欲与太祖皇帝决战。”
“此战中,陈友谅自恃艨艟巨舰,以火炮逞凶,太祖皇帝几遭不测,然天佑大明,适时东北风起,太祖皇帝当机立断,改用火攻,焚其战舰无数。”
“后值鄱阳湖水势渐退,太祖皇帝又出奇策,以轻舟之便,分兵合围,终使陈友谅中箭殒命,汉军遂溃。”
“太祖皇帝乘胜进围武昌,尽收湖北之地,正式晋位‘吴王’,建百官司属,然仍奉龙凤年号,以小明王诏命与吴王令旨并行,以示尊奉韩宋正统。”
“旋即再度亲征武昌,迫使陈友谅之子陈理势穷出降,继而我军势如破竹,连克庐州、吉安、衡州诸城,复取宝庆、赣州、浦城、襄阳。”
“遂传檄四方,兴师讨伐张士诚,先克湖州,再破杭州,及至兵临平江,张士诚犹作困兽之斗,巷战竟日,终至力竭被俘,至此江南一统,大业始成。”
“太祖皇帝虽已雄踞江南,却仍念红巾军旧义,尊奉小明王为帝,遂遣廖永忠赶赴滁州,迎小明王至应天。”
“然天意难测,小明王渡江至瓜步时,竟遭舟覆之厄,不幸溺亡,自此,太祖皇帝始改元更制,将小明王身亡的第二年称为‘吴元年’,不复沿用龙凤年号。”
“后世对此事议论纷纷,一说太祖皇帝当年亲赴安丰解围,名为救援,实为夺取小明王,得此‘宋室正统’在手,既可借韩山童反元大义之名,又可暂缓称王之议。”
“更有一说,是谓小明王沉船之事非出偶然,小明王虽为共主,却已成太祖皇帝称帝之碍。”
“廖永忠奉命行事,于瓜步渡口制造意外,为太祖皇帝廓清大统之路,此事虽无明证,然观其后改元建制之举,不免令人心生疑窦。”
张祁叹道,“廖永忠此人,早年便以豪迈果敢著称,元末乱世中,他与兄长廖永安在巢湖聚众结寨,后率水师归附太祖皇帝。”
“正是得益于廖氏兄弟统帅的巢湖水师,使得太祖皇帝得以在马场河首破元军水师,扭转了江南战局。”
“此后巢湖水师屡建奇功,不仅在江上屡挫元军锋芒,更在攻取应天之役中建下首功,可以说,若无巢湖水师相助,太祖皇帝断难在江南与陈友谅、张士诚形成鼎足之势。”
“可惜太湖水战时,因援军延误,廖永安孤军奋战,终至兵败被俘,张士诚素重英雄,欲以高官厚禄相诱,百般劝降,廖永安却宁死不屈,终在囚禁中郁郁而终。”
“此后廖永忠继领水师,与徐达、常遇春配合无间,鄱阳湖大战时,陈友谅麾下猛将张定边险些置太祖皇帝于死地,正是廖永忠与常遇春合力相救,方转危为安。”
“其后在泾江口,又是廖永忠截断陈友谅退路,助太祖皇帝奠定胜局,待陈理在武昌称帝,廖永忠再建水寨封锁江面,终使陈理不战而降。”
“论廖永忠之功勋,可谓冠绝诸将,自鄱阳湖救驾之殊勋,至平定四方之伟绩,其战功彪炳如此,实无需行此险着以媚上,然正因其功高盖世,后世谓其奉密令溺毙小明王,反倒顺理成章,何其讽刺?”
其实张祁认为于谦拿廖永忠举例并不十分恰当。
后世史家之所以认定廖永忠是奉朱元璋之命杀害小明王,实因小明王溺毙后,朱元璋仅对廖永忠进行了口头上的象征性申饬,没有任何实质处罚。
而且小明王之死使朱元璋得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义军最高领袖,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最终获得最大利益的都是朱元璋。
廖永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效忠”得太过火了。
倘或廖永忠是奉密令行事,则意味着他掌握了朱元璋的致命把柄,若系其擅自揣摩上意而为之,则暴露出其越权行事的同时,更将弑主恶名强加于朱元璋身上。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注定会令朱元璋对这位“过于能干”的臣子心生芥蒂。
但眼下张祁面临的困境截然不同,他本性善良,远不及朱元璋那般城府深沉、手段狠辣。
他甚至能完全理解王竑当庭殴打马顺的冲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王竑实在是“太想进步”了,对仕途晋升的渴望实在太强烈了。
张祁并不想断送王竑的仕途前程,他只是希望今后臣僚们能够谨守本分,依令而行,而非动辄妄加揣测君心,甚至假借“效忠”之名行杀戮之事。
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越界的“忠诚”,有时候比明目张胆的抗命更为可怕。
于谦却笑道,“殿下如何觉得讽刺呢?小明王溺亡未几,太祖皇帝旋即正位称帝,开创大明基业。”
“彼时廖永忠虽遭疑忌,却仍被委以重任,转任汤和副将,先平浙东方国珍,再定闽地陈友定,继而扫荡粤东邵宗愚,又剿灭盘踞广西的蒙元余部,最后与傅友德会师巴蜀,一举荡平明夏。”
“虽名义上以汤和为主帅,实则多赖廖永忠独当一面,尤以平蜀之战,廖永忠与傅友德珠联璧合,太祖皇帝写《平蜀文》时,亲口赞誉‘傅一廖二’,其后更是北伐蒙元,肃清漠南,靖海平倭,威震东南。”
“太祖皇帝虽恼廖永忠擅杀小明王,却仍予其建功立业之机,大封功臣时,更特意提及鄱阳湖救驾之功,赞其为‘奇男子’,须知终太祖一朝,得此誉者唯元廷王保保与廖永忠二人而已。”
“这般用人气度,方显帝王胸襟,殿下若欲成明君,当效太祖皇帝用人之智,臣子效忠,纵偶有过当,亦当以宽宏待之,若因小过而拒忠良于千里之外,岂是圣主应有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