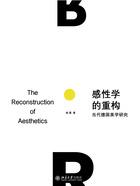
第一部分
当代德国感性学理论
第一章
显现美学:此地与此时的游戏
(马丁·泽尔)
一种好的美学,总是一种好的哲学;一种好的哲学,总能走向一种好的美学。如果我们同意德尔菲神谕以及苏格拉底著名格言所表达的原则,把哲学看作对人类经验的所有可能领域做出普遍性反思的事业,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对作为人类经验基础的感性领域有所重视。这种“重视”,不在于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感性领域如何进展到“更高的”思辨领域,也不在于从伦理学角度探讨感性领域如何被意志驱动成为行为的开端。毋宁说,这种“重视”是对一个经验领域独立价值的思考——这正是鲍姆嘉通“感性学”致力于强调的问题,从他这里开始,美学的探讨超出了对趣味标准的经验论探讨,以及古典主义对“诗学”的研究,从一种零散的批评集合体,进化成自觉与其他经验领域相参照而获得其独特哲学坐标的学科。按照鲍姆嘉通的说法,这种独立性主要来自对“个别”而非“一般”的关注,[40]对个体事物之感性丰富性[41]的关注。它固然是一种“低级认识论”[42],但却是不可逾越,也不可替代的领域。到了康德那里,鲍姆嘉通思想中的不彻底性被抛弃了,审美被明确表述为与认识及实践相区别的独立领域,它的意义不在于促成认识,而在于“认识诸能力间的自由游戏”[43];不在于实践,而在于获得一种(暂时的)“不确定”[44]。以后的重要思想家,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席勒、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都对哲学美学倾注了热情,无论他们的意见分歧多大,各自对该领域的定性如何,都是在鲍姆嘉通与康德所厘定的基本视野之上,对人类经验中既区别于实践又区别于认识(很多时候又以此融合了二者)的感性领域做出反思。
马丁·泽尔正是这样一个卓越传统的继承者。他不仅致力于在“美学地位相当边缘”[45]的时代,恢复(重构)美学在哲学中的合法席位,甚至在极其审慎的分析中,彰显美学的优越性。当然,泽尔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巨大的。一方面,语言分析方法的盛行似乎瓦解掉了不仅美学,也包括哲学的形而上学出发点,无论是康德的“先天立法”还是鲍姆嘉通的“完善性”都遭受了挑战。而另一方面,20世纪先锋艺术的发展,屡屡对艺术经验中的“感性”成分做出了有意的驱逐,也使得“感性学”面临丧失核心研究对象的危险。20世纪末叶的美学家,若想重构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美学,就必须从方法上吸纳分析哲学的语言自觉,从内容上兼容当代艺术对传统的背弃与逾越。
应对这种挑战,泽尔跟他同时代的许多理论家一样,[46]所采取的策略更多是“描述”的方法,而不是“规定”的方法;更多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演绎”的方法。这让显现美学既显示出分析哲学训练带来的明晰性,也体现出德国古典哲学寻求统一性的精神。也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广义的现象学方法,[47]它的判断不来自原则,而来自对经验事实直接而审慎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