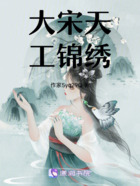
第21章 汝州
张方平见皇帝神色微动,忙道:“我与陆衡从前已有恩怨,而今不过是他挟私怨弹劾,且其《均徭役疏》欲改三司征科之制,实为乱法!“
仁宗揉了揉太阳穴,挥手道:“军籍事着枢密院与三司共查,征科之法暂不更改。“
仁宗顿了顿:“至于陆衡。”
张方平佯作忽然想起,从抽屉里取出一封密信:“巧了,今日收到汝州知州急报,言当地胥吏私吞青苗钱,正需能员整顿。陆翰林既然深谙民政,不如外放试之?“
仁宗一手撑额,闭了闭眼,思量片刻后:“既然汝州缺知州,那他去历练些时日吧。“
陆衡站在州桥畔,望着东流的河水,袖中官诰被掌心汗意洇出褶皱。
身后传来马蹄声,转头便见都水监的青盖马车停在柳树下,车帘掀开时,沈清荷官服裙裾扫过碎石子,腰间悬挂的铜鱼符随步轻晃。
“沈掌固今日不去监修汴河堤?”他抬手作揖,目光掠过她鬓边沾着的柳絮。
沈清荷回礼时,知他心情不佳:“闻说陆大人明日离京,特来送件物事。”
话音未落,小吏已捧上朱漆木盒,掀开时发现竟是仁宗御赐的鎏金铜龟符,“都水监着汝州府协修颍水故道,这符可直达水部衙门调阅档案。”
陆衡指尖抚过龟符上“制诰之宝”的印纹,嘴角露出一个宽心的笑容。
“颍水连年泛滥,去年决堤冲毁三十里农田。”沈清荷忽然开口,目光投向汴河上往来的漕船,“都水监测算过,若疏通故道引入汝水,可解下游水患。只是...”
她顿了顿,指尖在木盒边缘轻叩,“汝州士族多占河滩为田,恐有阻力。”
陆衡听得明白,此去汝州,治水便是头等要务。他抬眼望向远处虹桥,驼队正踩着青石板缓缓而过,货郎担上的拨浪鼓声响此起彼伏。可自己这一去,不知何时再闻汴梁蝉鸣。
“掌固放心,”他将龟符收入袖中。
陆衡的视线停留在她脸上:“清荷,多谢你。”
沈清荷神色不自然的别过脸去:“无事。”
“就当历练了,不日你定能调回汴京。”
陆衡离京那日,张方平在三司使廨院接见汝州通判。这位被他安插的亲信呈上密报:“陆衡已过中牟县,所带行李唯有书箱五口,未见金银。“
“书箱?“张方平拨弄着案头的和田玉镇纸,“他在翰林院时,曾借阅《唐会要》中'租庸调制'数遍,怕是想在地方试什么新政。“
“大人多虑了,“通判赔笑,“汝州乃京西穷州,去年遭蝗灾,三司又催缴上供米,纵是诸葛亮也难施展。“
张方平摇头,目光落在墙上《汴京赋税图》上,汝州所在的京西路被朱砂标得通红:“陆衡若在汝州做出政绩,他日必成心腹大患。你回去告诉知州,就说三司新定'预借法',今岁秋税须提前半年征收。“
通判大惊:“提前征收?百姓哪来的粮食?“
“要的就是他无法安民。“张方平冷笑,“若他抗命,便是违逆三司;若他催征,必失民心。无论怎样,这颗钉子都得拔了。“
九月初,汝州城秋风尽起。陆衡站在常平仓前,望着吏员打开的仓廪,里面堆满了掺杂着泥沙的陈米,散发着霉味。
“这是三司拨来的赈济粮?“他抓起一把米,泥沙顺着指缝滑落。
仓吏跪地哭道:“大人,三司说汝州去年歉收,今岁的常平仓粮已'预借'给东京厢军了。“
陆衡忽然想起张方平在朝堂上的话,冷笑道:“国用在先,民瘼在后。“
他转身望向城外,隐约可见逃荒百姓搭的窝棚,忽问:“州中富户可有余粮?“
“富户?“吏员苦笑,“李员外家的粮囤早被三司的'和籴'买空了,说是供汴梁权贵过冬用的。“
当晚,陆衡在知州衙署写下《请缓征疏》,请求三司暂缓征收汝州秋税。忆起汴京百姓“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的盛景,可眼前的汝州,连社糕的麦粉都难寻。
忽有衙役禀报:“三司度支院遣人来监收秋税。“进来的竟是张方平的亲吏王得中,腰间悬着三司铜鱼符,开口便要调发民夫二十万,运送漕粮。
“汝州丁壮已十去七八,“陆衡按住桌案,“再征民夫,田里的麦子谁来种?“
王得中冷笑:“大人是要抗命么?张大人说了,若汝州完不成上供,便劾你'玩忽国计'。“
陆衡盯着对方腰间的鱼符,忽然想起:“三司使掌邦国财用,位亚执政“,这鱼符便是张方平权力的象征。
他解下自己的银鱼袋拍在桌上:“我这知州银鱼袋,今日便押在你处。待我凑齐漕粮,自去三司领罪!“
王得中咬了咬牙,只好作罢,将情况上报给张方平。
张方平便将此事掐头去尾上报给今上。
……
一月不到,陆衡转任颍州,刚到任便收到张方平的三司札子:“着颍州每亩加征'拔钉钱'五十文,充作宫廷修缮费。“他查《颍州田籍》,发现所谓“拔钉钱“竟是五代时吴国旧税,本朝早已废除。
“这是张方平故意刁难。“幕僚陈子谦指着札子上的“特旨“二字,“三司使若想整人,有的是祖宗旧法可用。“
陆衡却展颜一笑:“既是祖宗旧法,某便依祖宗旧制办。“
他命人取来《庆历编敕》,在“杂税“条目下朱笔圈注:“凡旧税已蠲者,不得复征。“
次日,颍州城门张贴黄榜,宣布废除“拔钉钱“,并将三司札子全文公示,旁注“有敢私征者,许民扭送州衙“。
消息传到汴京,张方平正在枢密院与文彦博对弈。听完密报,他捏着的黑子“啪“地落在棋盘外:“反了!竟敢公示三司文书,这是打老夫的脸!“
贾黯扫了眼棋势,白子已将黑子逼入死角:“陆衡在汝州开仓赈济,虽违三司令,却得了百姓口碑。如今在颍州又借编敕抗命,恐有结党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