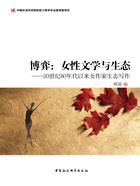
四 进入中国本土生态女性写作研究的视角与途径
看来,需要对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的概念予以认定。而这个概念是基于中国女性生态书写的本土现实,是否要回应西方生态学的理论阐述,是否要接续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文脉,笔者不想做简单的概念模仿,只想切合笔者的文本考察与解读,做出自己的理论表述。
当然,笔者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地了解女性文本,以能够从个案研究的微观研究开始,依次渐入宏观视野中。笔者着力从生态视角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有影响力的文本,还有那些由于历史、文学制度、史料等影响而不被重视的女作家文本,这样能够获得包含有生态价值判断的女性文学史实。
在这里,首先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存在,即西方生态理论本身仍然是一个小于女性文本的存在,有关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本身的生态诉求,还存在异议。
一类以王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摇摆的概念,甚至有附庸风雅之嫌,“揭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目的究竟是为了丰富发展以前的批评,还是为了强化壮大新生的生态批评?虽然无论出于哪一种目的都有其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的价值;但也应当看到,基本目的和主要诉求上的辨析,是将特定的批评进行学理性归类的必需。比如,有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转而倡导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有许多观点是与生态主义的基本精神相悖逆的。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不能仅仅因为她们自称‘生态’、涉及生态就简单地将她们的研究归类于生态批评。我们需要辨析:她们如此热衷地研究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是从女性的角度探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根源,从而丰富强化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推动生态批评的发展,进而为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呢;还是为了从更广的范围、更新的角度,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危机,来进一步探讨人类社会压抑女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制度,从而更加确立女性主义,更好地弘扬女性意识,更有效地凸显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呢?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生态批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生态批评(简称女性主义的生态批评,中心词是生态批评);如果是后者,我们则要说那仍然是一种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了生态批评某些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简称生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心词是女性主义批评)。”[20]
另一类以鲁枢元为代表,继1996年关春玲在《国外社会科学》中率先介绍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各个流派之后,极力主张打造中国的女性生态主义理论。他在其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中辟专节论述了女性、自然和艺术的关系。他在分析了马克斯·舍勒的女性主义观点后不无正确地说:“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严重流丧、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同年出版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也抓住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策略,指出其“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
王克俭指出:“在生态文学研究方面,我们当前的眼界似乎也狭窄了些,尤其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已把‘生态文学’命名为‘环境文学’,这就使这种文学的题材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之中,这样的关系还是比较肤浅的。而当把这种文学命名为‘生态文学’之时,我们的视野就可以提升到自然文学与精神生态的高度,注视一切生命的自然状态与精神状态,在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高度作出审美观照。”[21]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自身则强调对自然的占有和对女性的占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即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来自一种父权制的世界观,也正是这样的世界观确立了其统治妇女的合法地位。胡志红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发展中的批评理论,它借鉴、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策略,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自然、阶级、性别及种族四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开放式、包容性的文学批评,正在向国际多元文化的趋势发展。它试图揭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人对妇女的统治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致力于探讨二者获得解放的策略与途径,凸显自然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22]
显然,由于持不同立场的派别丛生,引起了学界一些争议。而生态批评界也逐渐认同了女性参与自然危机、人的精神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等的主观倾向与价值认同,因为在人类发展意义的高度来看,男女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生态差异,彼此又同在生态系统的链条上。
即便我们承认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强势传播,但在面对中国女性写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现象还是发生了:削足适履的嫌疑。因为,生态批评思潮相对于女性写作依然是滞后的,依然不能够穷尽我们中国本土女作家的生态书写事实,因为这是在中国。
所以,笔者不想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裁剪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因为理论本身由于历史、文化、现实等存在异质性,同时移植的过程中也多有歧义,更因为两者本来就不是同一的话语系统中的生成物。事实上,按照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也囊括不了西方女性本土生态写作的全部。理论本身是后于写作的,存在先天的局限性。同时,为避免庸俗的社会学之嫌,笔者对女性生态书写是基于两点来考察的,尽可能在生态文化视域下考察女作家的写作:一个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生态书写,一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精神生态层面上的亚生态叙事。基于生态学的严格意义,笔者提出一个设想,认为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书写是介于生态学与社会学、精神学意义之间的一种侧重对女性本体价值观立场、生命形态与精神形态予以表达的话语方式、叙事方式,以体现多种学科交融之后的共生。自然,进入生态叙事的女作家文本有别:一是贴切的女性生态文本,一是泛化的生态女性文本。按照这种延伸,可把中国本土的女性生态书写划分为:自然性的生态写作与社会、精神性的生态写作。而女性生态书写,就是指女作家以生态视角,对自然、社会与精神界面的价值判定与表达,强调女性追求个性发展,也恪守与男性、社会还有自然和谐的生态美学原则。
其实,这两个界面,存在有本质的同一。原因在于自然—人或自然—女人,把人与自然当作两个世界的交锋与和谐,按照中国传统“易经”将宇宙万物归结为“阴阳相生”、佛学中“众生平等”的思想以及深层生态学的观点,自然与人一样有存在的理由与利益,而人的阴阳相生与万物的阴阳相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把人作为一种自然属性来考察的话,男女的性别也便是自然的存在,只是由于社会性的原因,才有了社会性别之说。女儿性、妻性与母性,在生态意义上,是没有性别的;而在政治与现实中,则有男性与女性的异同。
依此来看,当今活跃于文坛的蒋子丹、迟子建、方敏、叶广芩、萨娜等就是典型的女性生态作家,而张洁、铁凝、王安忆等的书写,也不失为在社会生态(含有性别生态)或精神生态界面上展开的追踪。但倘若从严格的生态学理上去追究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上,生态书写是一种融合了宗教、文化、自然、社会、人类意义上的“间性智慧”的表达,有时候概念本身也存在着审美的模糊性、游离性与外延性。
倘若从生态文明的高度来看,不管是基于何种立场与表述,只要是站在人类发展高度,为消除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竭尽所能的所有跨文化的间性智慧,都是有益的。生态文明应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形态,它反映的是建立在人与人利益关系协调发展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协调共生关系。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外在基质,精神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内在价值追求,社会生态则是生态文明的制度本源。在笔者理解中,自然、社会与精神只是生态文明的三个维度,因为前瞻性的生态文明,是一个颠覆原生态文明、前现代化文明的崭新的文明形态,它容纳有新的质素,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被称为生态鼻祖的蕾切尔·卡逊在《感悟奇迹》一书里写道:“孩子的世界是新鲜而美丽的,充满着好奇与激动。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假如我能够感动据说会保佑所有孩子的善良仙女,我将请求她送给世上每一个孩子一份礼物,那就是永不泯灭的、持续一生的好奇,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免疫力,用以抵抗未来岁月里的乏味、祛魅,抵抗那些虚假而枯燥的先入之见,抵抗背离我们力量本源的异化。”[23]蕾切尔·卡逊也认为,人的力量本源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充满友善与爱,而当代人也只有真正地消除反生态的文明对人的异化,才可能重建新世纪的生态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确应该回到智慧的童年,回到生命原初精神,来反思、审视我们的生存现实及内心世界。
正是基于如此的哲思,确认了生态女性写作的本身内涵与外延皆是宽泛的,在梳理了西方生态女性理论起源、发展以及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阐明了本土生态女性写作研究的意义、视角与途径的基础上,本书力求从多个视角、视域、立场来看待中国当代生态女性写作,从中国生态女性写作的背景与资源做出了阐释,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崛起,到90年代后期乃至到21世纪,中国逐渐进入了消费时代,女性文学与生态之间存在博弈。跟踪女性生态写作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指出女性文学的悄然转变,即由激进走向了缓和,由个体走向了群体,由西化走向了本土。同时,发现由于基点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以及价值立场、话语方式与叙事的不同,中、西方女性生态写作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的美学形态与内在切换,体现为原始生命形态的寻找:自我生命本体与原乡自然生命形态的容纳与契合;女性自然性征的强调:作为性与生育的工具;女性寓言:母性生命形态与女神的原始精神追随;日常生活场景展示:女神形象与女性母性的有机结合。随之,女性生态写作的主体姿态有:激进的生态意识女作家群,温和的生态意识女作家群与原生态女作家群。在新媒体时代,女性写作面对多重资本与媒介的侵入,存在生态与资本博弈,导致本土女性生态美学的建构或流变,被拆分三个板块:自由书写模式、摇摆于市场性和介入性之间的“写作模式”、作为自我消费符号书写。由此,本书指出女性生态写作的路标:女作家从生态学视角,立足本土,秉承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突破本土的视野走向世界,恪守与男性、社会还有自然和谐的生态美学原则,体现审美生态追求的多样化,旨在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与文化根源,也在寻找着女性在自然、社会中的重新定位,并从中发掘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建构的特质,以及中国女性文学乃至中国本土文化的生长点,捕获女性生长与中华文化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因子。说到底,女性孕育了人类,也孕育了历史,更构建了文明世界。这一切,都将变得有价值和意义,并且切实可行。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2] 最早由勒特(Reiter)于1865年将两个希腊词:oikos(家园或家);logos(研究)组合而成。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首次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科学。
[3]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12.
[4] Karl Kroeber,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6.
[5]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朱坤领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肖巍:《女性主义伦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7] [美]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前言: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8] Guttman,Naomi.“Ecofeminism in Litemry studies”,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2.
[9] 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0] 曹南燕、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
[11] 陈喜荣:《生态女权主义述评》,《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2] 李慧利:《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13] 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2期。
[14] 肖巍:《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15] 王建元:《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6] 陈霞:《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8期。
[17] 李瑞虹:《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18] 曾繁仁:《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
[19] 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20] 王诺:《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6期。
[21] 王克俭:《生态文艺学:现代性与前瞻性》,《文艺报》2000年4月25日。
[22]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23] 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pp.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