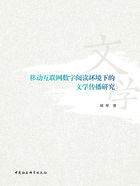
导言
当文学作品的传播,可以无时空限制地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延伸,阅读环境的变革对文学传播的深刻影响,不言而喻。就移动数字阅读平台的出现而言,“最初看来,这个规模巨大、无处不相连的新平台就像我们传统社会的自然延伸。它似乎只是在已有的面对面的关系中加入了虚拟关系——我们只是在网上加了几个好友,扩大了朋友圈,增加了新闻的来源,让我们的行动更加数字化。但事实上,就像温度和压力慢慢升高,当这些事情持续稳定地发展,我们会到达一个拐点,或是一个复杂的零界点,在这里,变化是不连续的,于是相变发生了——我们会突然处在全新的阶段。那是一个具有新常态的不同世界”[1]。这个“具有新常态的不同世界”就是一个可以在移动中进行数字化阅读的全新世界。人们可以在面对面社交之外,凭借自己的审美偏好来建设自己的虚拟朋友圈,还可以在移动数字阅读行为中对大量文字信息轻松复制、粘贴,再进行传播。移动数字阅读技术不但赋予了大众传播权,还为大众的传播内容生产能力带来了增值。
显而易见,除去书本、报纸、杂志,这些可以移动的智能终端已经成为大众接触文学、阅读文学、协同书写的一个重要入口。移动数字阅读作为一种相变带给文学传播的,不仅是阅读载体及阅读方式的改变,还有文学传播载体的更新与扩容。一部文学作品进入大众传播视域,不单只是印刷文字形态,还会有影像形态和声音形态的显现,当文学作品具备了一定的受众认知度和影响力,在传播过程中就可以跨媒介创制并衍生出一系列文本。因此,本书中的文学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在新阅读环境中有了新的延伸,不光是中国文学作品(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印刷文本形态,从文学作品印刷文本出发跨媒介所创制的其他文本形态,也会进入到本书的观察视野中来。
就传统文学研究视域而言,笔者在爬梳中发现,作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心,社会和读者这两个维度早期主要是侧面进入文学研究,作为作家、作品研究的语境性探察的补充性添加。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作家研究很难逃开外部社会综合系统的照拂,文学作品研究却曾经走到了极致,这就是在20世纪发生的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形式主义、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本体研究方法论的风起云涌,加上同语言学的亲密联姻,使得文学作品研究通过对文学内部形式的深入探掘,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研究闭环,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形式主义的研究当然是片面的,但在揭示某些文学内部规律方面却有可资借鉴之处,某些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诸如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隐喻、反讽、象征、叙述观点等艺术技巧,不同文学体裁的区别、联系和发展等,比起前代人,显然是大大地深入了,有不少是精彩而独创的见解。”[2]
然而,文学作品内部的形式主义研究只是作品研究的一种类型,文学作品的内部形塑要素多元,形式主义要素被包蕴其中,却绝非唯一要素。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一开始更像是对文学研究多年来聚焦外部系统运转的一次研究类型学上的反拨,但是它也确实为文学研究的内部体系建设破出了一条相对规范化的路径。从西方到东方,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发生着延展和深化,所产生的文学话语也不断参与到与当下问题的和解中去。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说[3]标示世界(社会)与文学接受(欣赏者)这两个维度作为与作家、作品并置的文学要素已进入文学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