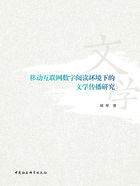
第二节 文学接受研究:普通阅读者和专业阅读者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文学研究主要还是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对世界(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作家的生活背景、作品的写作环境研究,不是文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文学接受研究在当代中国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文艺研究》刊发了周宪的论文《现代西方文学学研究的几种倾向》,文学接受研究在其中被浓墨重彩地论述。1985年《文艺研究》第6期刊发了周始元的长文《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的再创造作用——现代西方文论中的一个新课题》,我国学界文学接受研究的筚路蓝缕从此开始。文学接受研究主要是研究文学读者(受众)的文学接受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处于真空环境,而是在某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所以文学接受研究也需要对社会历史环境进行照拂,但这种环境照拂和文学社会学研究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功能性的,扫描社会历史环境的旨归是为了更清晰地把握读者的文学接受过程;文学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历史环境的深描是结构性的,文学活动全程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会受到具体语境的制约,文学社会学研究里的社会历史性探掘就是在结构性层面上阐析这种制约是如何成形的,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在何种层面上参与了文学活动的塑形。
一 普通阅读者
通过文学接受研究领域的耕耘实现文学理论的更新,是学界文学接受研究的一个侧重点。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个主要是文学理论畛域的扩伸,比如1992年6月出版的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借助高等教育教科书管道为文学接受理论开疆辟土,之后国内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几乎很难避开对文学接受理论的探讨。另一个则是学者个体在文学接受研究上的具体论著,比如朱立元的《接受美学》、金元浦的《接受反映文论》、王岳川的《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等文学接受研究论著。
不过,这些教科书与研究论著所聚焦的文学受众几乎都是专业阅读者(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作家),这些专业阅读者对文学的具体接受和文学评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对象,进而被建设成为一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但是,更广大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普通读者,“比如专业学习者诸如文学研究生,普通大学生,中小学生,他们在文学课堂和课外语文课堂和课外的阅读,也应该是文学接受的重要部分,还有工人读者、农民读者、商人读者,他们对文学的阅读则是文学接受更重要的内容,更能够代表普通文学消费意义上的接受”。[19]21世纪以来,语文教育进入文学研究视野,拿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围绕语文教科书的编撰与改编展开,语文教育的具体对象——中小学生的具体文学理解和文学接受依然没能进入文学研究视野。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普通读者的文学理解和文学接受材料难以收集,即使有研究者筹划收集,也无法给出一个较为权威或者合理的样本采集标准。到底是以某一具体历史时段为普通读者阅读材料定量采集的时间段落,还是从文本诞生伊始就开始采集?前者的话,择定某一历史时段的标准在哪里?后者则时间无涯,材料采集茫茫无边,难理头绪。就算为某一具体历史时段的普通读者阅读材料采集定性,普通读者人群又异常庞大,如果想全类别采集,这个全类别的“全”是否能够覆盖全部类别?如果甄选出某一读者人群为具体研究样本,这个甄选标准又是不是能经受住检视?
当然,就算上述问题都被顺利解决,对普通读者个体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的材料收集,也会陷入一个难题当中,那就是读者个体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不能像专业阅读者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一般,顺利借助把关人的放行,在公共领域获得充分显现。文学研究者之所以聚焦于专业阅读者的文学接受体验,大体上也是由于他们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大多可在印刷文字这一公共领域中进行追踪,国家图书馆的印刷出版物馆藏之全面,基本能够应对普通印刷出版物的检索。古籍善本的影印工作,也一直在进行时中。总之,专业阅读者的这些文学接受体验,无论是日记体、札记体,还是期刊报纸上的专篇或短语,只要付梓印刷,就进入了与他人共在的公共领域,也就有了被研究者追索到的基本前提。
相反,不能在公共领域获得显现的那些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体验,就是在相对于公共领域的“私域”生成的,同样以文字存留,它们却因不能见诸公共出版物,失去了被研究者追踪痕迹的机遇。不能见诸公共领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有诉诸公共出版物的尝试,却被把关人横刀拦截,未能如意。“只有那些被认为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值得被看和值得被听的东西,才是公共领域许可的东西,从而与它无关的东西就自动变成了一个私人的事情”。[20]把关人拦截的标准,就在于这个“被认为”和“值得”,当然,标准的拟定者,是把关权力关系中的持有方,与普通读者无关。阿伦特并不认为这些未被公共领域许可的“私人的事情”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她认为“公共领域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也可能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魔力,富有感染性的魅力,以至于许多人都采用它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阿伦特接下来却指出这“并不因此就改变这些东西本质上的私人性”。[21]可见,像阿伦特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为把关权力关系中的既得利益方,即使肯定那些不被公共领域所认可的“私人的事情”的价值,也不会随意将其接纳到公共领域中来,因为在她眼中,“公共领域可以是伟大的,但它却恰恰不能是迷人的,原因就在于它不能容纳与之无关的东西”。[22]
这种关于伟大和迷人的区分在公共出版物把关人那里随处可见,没有固定的区分标准,随之时代更迭和把关人的个体属性区隔会有变化,但是他们却凭借标准制定者的身份一直持有着把关人权力,来裁决从文字到文本的结果生成。所留下的,必是与他们的标准相符,反之,就是因不相符而不被接纳。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公共出版物都执着于同一个审美把关标准,也有公共出版物对普通人在私域发生的文本内容颇有兴味,给了专栏以公开显现。泛文学杂志《天涯》自1996年改版以来,增加了“民间语文”栏目,栏目中收集了日记、书简、记录、汇报、契约、文案、词汇歌谣、网络文本、启事、调查报告、吊唁挽词等文本内容,致力于民间语文的多元内容呈现。不过,细看《天涯》的“民间语文”栏目所刊发的内容,其所传递的是民间语言表达的斑斓样貌,还是语言表达的内容本身,而非民间阅读者的阅读接受。普罗大众文学接受的丰富体验,至少在公共出版物上,极少获得公开显现的空间,少量的读者来信,也多半是因成为出版编辑的某些想法的代言而被选中。换句话说,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本就是良莠不齐的荒原春草,土上现形的枝叶和土下埋藏的根茎也各有不同,只要进入劳动者视野,就会在他们的铲锄下,变得高低近似,身形相类。这种铲锄的过程,在一些老出版人的札记、访谈或回忆录中会见录一二,绝大部分都散作烟尘,那些荒野春草原本的良莠,文学接受研究者自是无从得知。
第二种是这些文学理解和评价生于私域,没于私域,从始至终书写者本人就未打算诉诸公共出版物。这种颇具偶发性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的生成和消失,在普通读者那里应是大部分。和第一种被把关人拦截而不能如意相比,结果虽然一致,都在私域彻底沉没,但是第二种文字记述更具备个人生活的无功利性,不诉求个人声音的公共显现,严格说来这种远离共同世界的表达,也随之丧失只有在共同世界才会彻底拥有的实在性。
当然,文学接受研究者也可以试图绕过印刷出版物把关人的拦截,通过社会科学的数据采样收集法直接面对普通读者,比如样本户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不过,样本户的甄选,还有问卷调查所采用的简化选择法,也容易把普通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杂生文学理解简化为一刀切,不能获得理想效果。
基于上述,印刷媒介时代,文学接受研究者对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体验的舍弃,一方面客观上是因为这些文学接受体验在公共领域的缺席,失去掉过头进行追溯的可能,另一方面主观上就算有研究者拿出材料收集的筹划,也因为无法归集而放弃。
二 专业阅读者
对比普通读者文学阅读体验的难以追踪,专业阅读者的文学接受体验的资料归集其实也并非易事,时代愈久远,难度便愈大。相较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接受研究在专业阅读者维度上的用力,得益于公共出版物的内容支持。现代文学批评家、现代文学研究者、现代作家等专业阅读者的专篇文字、访谈、札记、序跋、回忆录等,记录的点滴文学理解和文学评价,因为在不同公共出版物中的断续显现,有了具体追踪的基础,只要肯下功夫爬梳史料,终能理出些头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致力于史料学的学者,如陈子善通过对部分作家作品以及文论的辑佚,为现代文学版图的完整呈现殚精竭虑;如程光炜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语境的史料整理,力图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如洪子诚对当代文学体制性史料的爬梳,为我们揭橥共和国文学同政治体制间千丝万缕的关联,等等。这些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核和相关周边史料的辛劳整理,为文学图景在公共领域的丰富显现助力甚伟。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资料采集却难以完全借力于现代公共出版。历朝历代的古诗文以及专业阅读者对这些古诗文的评价,因为年代久远,在传世过程中,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被湮没尘间。当时藏书家们对这些文本和文学评价的辑录和刊刻工作,放到今天就是为后人守宝藏,功业千秋。没有历朝历代藏书家们的书稿刊刻在先,今天的公共出版完全不可能。首先,相当一部分古典诗文品评发生在文人社交现场,如果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且刻印成集,就会消散在历史现场。曹魏时期的邺城,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文人集团经常在一起宴饮,席中互相唱和诗赋,曹操的《短歌行》便是当时诗宴唱和的代表作品。建安文人间频繁的酒宴诗文创作,也促成诗文批评的兴盛,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最典型的代表。建安文人间的诗文评点,如果没有当时史书、文人书信记载,以及经藏书家编印成集传之后世,诗宴社交当中产生的诗文评论,当时便已消失,后世研究者也不可能有半点收集的机会。
其次,我国文人创造了丰富的笺注传统。历代文人喜好编选文集并加以笺注,这种传统既将历代佳作传承赓续,也能留下时人对这些作品的文学评价,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如果当时的文人笺注在历史烟尘中彻底佚失,那作品和评点也就随之消失。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在现代最为通行的由清代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被收录了22首,被收录数位于唐代诗人前列,可见李商隐在当时编选者心中的诗坛地位。宇文所安曾提到“李商隐的诗按说有两家宋朝的笺释,但都已经佚失了。在清朝以前,有一小批收录在选集和评论里面的对某些李商隐诗作的笺注和诠释”,之后到了清代,“1659年,出现了朱鹤龄更好、更全面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1762年的《玉溪生诗集笺注》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使用”。[23]李商隐诗作由宋代文人所做的笺注虽然佚失,却幸有后人继续对其诗作进行笺注,到了清代,竟成为诗评家诗作评点的重要对象,才得以继续存留诗名。显见,历代文人的笺注评点,因为在公共图书馆藏出现之前主要依靠私家收藏,佚失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后续文人没有接续作品笺注工作,其作品的文学评价甚至作品本身,都难以存续。李商隐算是幸运,那些诗文笺注彻底佚失的文人,或许连名姓都未曾留下。
再次,诗文选编笺注评点者的个人喜好和文坛地位也会影响这些文学评价在后世不同程度地存续。号称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在影视化形象呈现中,给普通观众多半留下狂诞才子印象。当然,普罗大众也并不关心学术研究中的唐寅文学形象,因为唐寅诗文写作还处于文言雅意是诗文写作文体的明代,对其诗文的阅读主要还是专业阅读者。20世纪以来专业阅读者对唐寅诗文风格的评价,与影像中的人物形象呈现,有趋同或不同,也基本是专业阅读者关注的话题,但是,专业阅读者给予唐寅诗文的文学评价发生的历史演变,所体现的专业阅读者的身份与个人偏好的形塑力量,的确不容小觑。现今学界发现的最早的唐寅文集是嘉靖十三年(1534)间的袁袠刻本,但因袁袠本人的创作风格受到明代茶陵诗派代表人物、复古运动的倡导者李东阳的影响颇深,文学主张趋同,[24]导致其对唐寅文集的编选也偏好复古风格的诗文,这个编选本只选了唐寅16篇文,32首诗。袁袠虽与唐寅生活在同一时期,并有往来交情,却没有将唐寅的全部诗文收入其选本,这其中自然就有本人审美偏好的缘故。之后,晚明文坛领袖袁宏道等人对唐寅疏狂风格的诗文颇为推许,加上明代著名藏书家何大成热衷于对唐寅诗文的不辍辑录,并有刻本《唐伯虎先生外编》《伯虎志传》《伯虎遗事》等传世,唐寅诗文的影响力可谓大为提升。何大成刻本不仅在唐寅作品收集上补上袁袠刻本的不足,还将一些明代文人对唐寅诗文的评价也收录,为唐寅作品与文学评价的后世版图的完整助力甚多。这里面,袁宏道是晚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领袖,反对拟古风气。在袁宏道去世后,后人将他担任吴县知县时收录唐伯虎诗文而编成的书刊刻,就是今天在唐寅文集汇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袁评本《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袁宏道在序言中写道:“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故余之评骘,亦不为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专以诗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为俗吏乎?”[25]袁宏道所言的子畏诗文“不足以尽,而可以见”,多少得窥他对唐寅的评价标准。因唐寅一生并不只有诗文,其与好友纵情书画、醉饮狂歌的放诞行为使得他在当时的众人中格格不入,而孝宗时“科场舞弊案”里唐寅的被构陷,更使他人生苦痛难消。在这般波诡云谲的人生历练前,诗文的确不足以尽,但可以见。袁宏道在袁评本中推许唐寅诗文中抒写性灵的部分,由于袁宏道的文坛地位,在后世文本传播方面,袁宏道所推许的艺术风格会在认知上得到强化。这也给后人留下了思考,那就是文本接受在专业阅读者那儿其实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像唐寅这样的作者,诗文风格并不单一,对其文学评价理应多元,但是他的复古文风和疏狂放诞文风,因为不同专业阅读者的不同审美偏好,在不同历史时期获得了不同的审美对待和传播待遇。这也说明了古典时代专业阅读者的文学评价中的审美偏好,对作品辑录、刊刻的形塑作用。
由此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传世过程中,必然少不了专业阅读者的文学批评、文学评价加以汇集的助力。艾略特说:“批评是帮助理解和赋予乐趣,理解一首诗就是有理有据地从中获得乐趣;不理解而盲目地享受等于从诗作中仅仅解读了自己的思想的影子。”[26]如果不执着于文学批评的学科性意义规范建构,让社会审美评析让步于学科性意义阐述,专业阅读者的那些吉光片羽的个性化文学批评、文学评价的确能够帮助大众从某一个具体层面来深入理解作品,甚至获得在作品阅读中破解谜团的乐趣。如果这种文本理解和破谜还做到“有理有据”,从作品阐释学意义上看,则是专业阅读者的专业贡献之所在。
专业阅读者因为阅读素养,一部分担任“全知全能的读者”角色,对于文本阅读中发掘的问题,将其他学科知识视野融汇进来,抒发个人特质鲜明的阅读体验。中国现代戏剧家、翻译家、学者赵景深在1927年写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中国新文艺与精神分析》中,就用精神分析法阐析了“绝口不提恋爱”的冰心女士:
我们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庐隐女士的小说十九描写恋爱,而冰心女士却绝口不提恋爱呢?如今在精神分析里可以得到解释。莫特尔把渥茨华士之爱自然看作性欲象征,我们也不妨把冰心女士之爱海当作性欲象征。母性般的爱小孩可以归入伊莱克察错综一类,爱她父亲又可归入耶的卜司错综一类。她是无时无刻不记念着她那横刀跨马的军官父亲的。如《繁星》七五说:
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
我要听你说你的海。
又八五说:
父亲呵!
我愿意我的心,
像你的佩刀,
这般的寒生秋水!
都可作为例证。她早年所作的《梦》也是纪念父亲的。不过在此应该向神经过敏的先生们声明,这安全是“不自觉”或“潜意识”的,并非露骨的性爱,更非见诸实行,这是常人都有的历程,并不仅冰心女士一人,所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的女作家并不见怎样的唐突。[27]
赵景深笔下的“伊莱克察错综”就是伊莱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耶的卜司错综”则是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术语。赵景深在这篇评论文章中对这两个术语的借用,其实并不准确,但是他用精神分析学视角来解读冰心的《繁星》,并认为这种“不自觉”或“潜意识”的爱欲书写,“是常人都有的历程”。在当时中国,这种跨界阅读阐析不仅能带来认识论的延伸,还能赋予知识跨界的乐趣。这种颇具个性鲜明特质的文学接受体验具备个人独断特征,但可以以文学阐释者的个体身份去丰富文学接受体验。
还有一部分专业阅读者没有将自己摆在“大读者”的位置上,而是做了一个批评性史料的记述者。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郭绍虞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上卷出版后不久,就在胡适的审定下成为教育部面向公众推行的大学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则因为国难的阻隔,延至1947年才获得公开出版。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都作为大学教材在中文系获得广泛应用,像文学批评史这种文学批评之批评,借助高等教育的管道,才会有自己更大的扩散空间。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从学科建构意义上看,处于专业阅读者文学评价阶梯的云端,因为需要对其他专业阅读者的文学批评做出评价,是文学研究者进行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接受体验书写。郭绍虞的文学批评体验的书写风格和赵景深的个性化阐释风格大不一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本著作中,郭绍虞的批评态度很鲜明,“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罗剔抉,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加以融会贯通,也费过一番经营擘划”[28],收集材料再融会贯通。这种努力持有客观立场、削弱个人主观论断的批评记述者姿态在郭绍虞的自述中更为凸显:“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29]
无论是赵景深这样的个性化阐释者,还是郭绍虞这种文学批评史料记述者,他们作为具有文学批评素养的专业阅读者,在公共空间显现的还是身为少数读者的个体阅读经验。如果将他们的阅读经验升华为文学体认的重要标准,并从中提取文学作品传世的价值要素,再加以合法化,却忽视其他更多的普通读者在社会历史浮沉中的文学阅读经验的话,最广大的阅读人群就失去了阅读主体性。他们在文学接受研究中的存在多半是一种社会背景设置,或成为历史的底色。这种脱离最多人群之文学阅读评价的社会历史性建设,其结果就是广袤且驳杂的文学接受状态变成少数读者的社会历史行动结果,文学接受的社会历史性考查也只是围绕着这些少数人群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