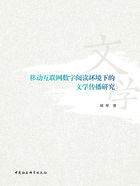
第一章 移动数字阅读环境的形成:从印刷场景到移动传播场景
2020年的春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侵袭全世界。全球民众居家抗疫的时刻,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英文版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BBC资深主持人兼撰稿人、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担纲这部纪录片的制片和撰稿。“‘杜甫生于8世纪的唐朝,对应英语文学传统,那是英雄叙事长诗、古英语传说《贝奥武夫》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盛唐的倾颓。’纪录片把杜甫放在历史视野和比较视阈中展开讲述,向英语世界的观众介绍杜甫的一生。”[1]
号称“诗圣”的杜甫在当今中国,借助国民教育体制,其部分作品在基础教育课堂成为所有学生的学习对象,加上各式媒介对其人其作的充分传播,是极具国民度的唐代诗人之一。这样极具国民影响力的优秀诗人,成为海外纪录片的叙述对象并不意外,以纪录片影像记录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在电子影像传播早已历经数十年发展的今天,也绝无稀奇之处。但是,记录杜甫的这部纪录片是在 BBC 这家颇具影响力的老牌电视机构平台播出,这一点就会成为这部纪录片在网络和比特[2]云端获得扩散式传播的高基点,因为BBC已经先行替我们充当了权威“守门人”。换句话说,是 BBC 在数量众多的中国诗人、作品传播中替大家选择了杜甫。这种选择在人类虚拟欲望不断扩张的当下,是媒介机构在实体空间发出的声音,而BBC的平台之翼,则会让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和他的作品,以更丰富的方式跨语境传播到世界各地。
必须要说明,中国文学传播借助电视机构平台插上双翼,是20世纪80年代业已出现的话题。直到当下,中国文学的影视改编对文学传播的推动,仍是文学传播研究的话题之一。以英语纪录片形式在一个以纪录片质量著称的全球知名电视机构平台播出,对杜甫诗歌的当代跨境传播,其价值会尤为凸显。这其中最重要的症候,就是权威性选择在人类信息传播新过滤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信息传播新过滤机制的出现,源于信息选择机制的嬗变。互联网这个赛博空间的出现,让科技文明的强势助力,变得清晰可见。在赛博空间里,人们可以轻易绕过传统传播机构的壁垒,随心浏览海量数字资源,也可以不经把关人的审定,在互联网世界自由输出自己的文字观点、拍摄或剪辑的影像视频、制作的图像文本等。写作文本、在数字平台发表再成为作家的过程,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变得快捷无比。这导致原有的信息选择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被机构、组织垄断的信息生产权和发布权被稀释、分散到最广泛的普通民众那里,过去先经传统把关人审定、再在限定输出媒质中由普通民众被动选择的信息选择机制,在赛博空间发生裂变,赋予了普通民众在信息选择机制中的主体性。是普罗大众的自主同一性选择让部分信息被高频且广泛地显现在公共空间,而非相反。然而,这种信息选择机制的根本改变,却让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这个看似自由且自主选择信息的时代,陷入信息选择困难症的深渊。
因为,在2020年的人类世界,我们每个人都被海量信息缠绕着。正如凯文·凯利所言,在赛博空间,“我们来到了一个无限大的大厅里,在每一个方向,都堆砌着无数种可能的选择。尽管类似汽车无线电制造这种老旧行业被淘汰消失,但可供选择的职业种类却变得更加丰富了。度假的地方、吃饭的地方,甚至是食物的种类,这些可供选择的选项数量每年都在累加。可供投资的机会也在迅速增加。可供参加的课程,可供学习的东西,可供娱乐的方式,这些选项的数量已经膨胀到天文数字级别。在人们有限的一生中,没有人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个选择的潜在影响都逐个审视一遍。即使只是对过去24小时里被发明或创造出的新事物进行概览,也会花费我们一年以上的时间。这个包容万物的图书馆规模极其巨大,它迅速吞没了我们本就十分有限的消费时间周期。我们将需要额外的帮助才能穿越这广袤之地”。[3]这个“额外的帮助”就是凯文·凯利所说的“某些人或者东西来做出选择,或者在我们耳边悄悄地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4]。
传统印刷传播时代普罗大众在物理空间中的信息选择,是被管理和把控的,印刷传播的主体成为管理方与把控方,被他们过滤和选择之后的信息失去了真正的多元。耐人寻味的是,赛博空间中的人们,一旦被海量无边的信息包围,在注意力的时间刚需的催迫下,也会产生对信息过滤的理想系统的需求。不同的是,印刷传播时代的信息过滤系统被权力关系的施加方所把控,普罗大众只有被动接受被给予的选择,不能多加置喙;而赛博空间中的人们,对理想的信息过滤系统的期待,建立在主动需求的基础上。像BBC 这样以出品高质量纪录片著称的世界重要新闻媒体,就极有可能成为人们选用的传统信息过滤系统——权威性媒介的把关。
中国文学传播在当下,普罗大众面临着极其稀缺的注意力资源被信息过滤体系的混乱所劫持的困局。传播端、传播平台、传播内容生产方、内容输出者等,都有可能有着进入信息过滤系统,成为满足大众注意力刚需的理想过滤体系的野心。这些野心允许人们用两种截然相对的价值立场来具体面对。一面是传播学批判学派对这些野心背后的逐利主义目标的锐感,提醒人们对此提高警惕,是自然的反应。另一面,像凯文·凯利这样全身心拥抱技术文明的人,虽然也发现了问题症候——在打算进行信息选择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对自己并不是很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依赖过滤器来告诉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却依然乐观地认为:“它们(过滤器)并不像是奴隶主,反而更像一面镜子。我们会听取由我们自身行为产生的建议和推荐,这是为了听一听、看一看我们自己是谁。”[5]
这种信息过滤体系的混乱,自然不是一天形成,从印刷场景发展到移动传播场景,文学阅读场景的变换,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行为,从而改变了文学传播的形貌和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