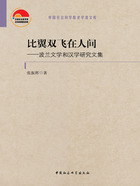
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是继浪漫主义文学之后产生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侧重于客观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力求真实再现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各种弊病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加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唯心主义的胜利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促使人们以更加客观的立场去看待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在文学中便产生了现实主义流派;如若再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和进行创作,就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波兰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由于这种压迫的加剧,1863年1月在当时被沙俄占领的波兰王国的首都华沙,爆发了著名的抗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迫使沙俄占领者于1864年在波兰王国实行了农奴解放政策。波兰王国农奴解放后,资本主义发展很快,与此同时,在华沙也产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实证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提出,在波兰,要尽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科学和医疗事业,进行城市建设和普及教育,反对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种族歧视,主张男女平权和社会各阶层平等。这个纲领提出的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经济的做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文学创作界,一些著名的作家如爱丽查[1]·奥热什科娃、亨利克·显克维奇、波列斯瓦夫·普鲁斯和玛丽娅·科诺普尼茨卡等最初也曾以为只要实行这个纲领,就能使长年遭受残酷民族压迫的波兰走向复兴,他们早期的作品曾对这个纲领的实施表示赞同。但是在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波兰社会中,实证主义者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并且对沙俄占领者妥协和投降,他们的纲领在许多方面都不能实现。人们看到的是,民族压迫日益加剧,社会贫富不均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大,下层劳动人民依然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上述作家因此开始对黑暗现实表示不满,把他们的作品转向了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当时在波兰文坛占主要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
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以小说创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在当时的波兰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爱丽查·奥热什科娃在谈到这种文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小说是人类智慧的混合成果”[2],它“不仅能反映,而且同样能创造它反映的那些为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把它们提高到能使音调和形态、相似和对照、前因和后果都能达到美学上和哲学上的和谐。”“每一部有才能而且能很好地展开的小说,永远是,而且只能是从对世界某种环境的观察中获得自己的构思。”[3]“小说的意义和优美是依赖于小说的构思和完成,同样也依赖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4]“一切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美的大小,是要由在作品中的典型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或人类现象的多少来决定的。”[5]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小说要表现的,归根结底是“整个民族的典型”,是“所有人的哭泣和欢笑、愿望和叹息、社会的衰落和兴盛”[6]。
亨利克·显克维奇(1846—1916)的创作针对当时波兰的社会状况,大都以他气势恢宏、具有史诗风格的长篇历史小说来表达他强烈的爱国、战斗和民主主义的思想精神。他认为波兰具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传统,她过去“发生过伟大的事件,出现过伟大的人物,那里有过令人振奋的东西”。[7]作家看到了现实的黑暗面,但他要通过再现波兰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事件、伟大的人物和令人振奋的东西,来鼓舞他所在的现实中的全体人民的斗志,去和占领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恢复波兰民族的独立。显克维奇也正是因为他所创作的这些“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8]的历史小说,于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波兰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伟大作家。
显克维奇于1883—1888年创作和发表的著名的历史小说三部曲中的《洪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部作品取材于17世纪50年代初,瑞典封建主入侵波兰,对波兰各阶层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压迫,波兰人民在国王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最终把侵略者赶出了自己的国土。作者在小说中首先揭露了战争初期侵略者在他们占领的波兰国土上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抢劫、屠杀、亵渎波兰传统的宗教信仰等种种罪行,使波兰人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灾难。正是这种残酷的压迫促使他们迅速觉醒,奋起反抗。后来由国王领导、爱国将领统率和指挥开始发动反侵略的战争,得到了波兰全体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很快就打败了敌人。通过小说中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可以看到,这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一是波兰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参与;二是国王在这次波兰反侵略的战争中,起到了团结和领导人民反抗侵略者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核心作用;三是波兰爱国将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正确无误的前线指挥。在战争初期,由于波兰过去长时期内忧外患,经济衰落、兵力不足,瑞典侵略军在波兰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占领了几乎整个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也被迫逃到当时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去了。有一部分大贵族甚至背叛祖国,投降了敌人,但社会下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和一部分中小贵族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反侵略的战斗。后来,因为瑞典侵略者相继侵犯波兰大贵族的利益,最初投降的贵族大部分又回到了反侵略斗争的队伍中来。由爱国将领统率的正规军发动的阵地战和运动战,配合农民、山民的游击战,“随时随地能化作汪洋洪流,使一切入侵者无助地陷入灭顶之灾”[9]。通过显克维奇在作品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他深深懂得,不论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只有人民才能够创造历史,但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可以起到团结各阶层人民抵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作用,在和平时期,他也能领导人民去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富裕的美好社会而奋斗。显克维奇认为这一切的获得都得依靠人民,而获得的一切胜利成果,也要让全体人民共享。
显克维奇在1900年发表的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情节与《洪流》有些相似,它描绘的是15世纪初一个侵占波兰北部沿海一带的日耳曼骑士团对当地的波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并且进一步入侵波兰内地以及邻国的立陶宛,波兰和立陶宛两国因此结成联盟,奋起反抗,在1410年,两国联军在格龙瓦尔德打败了骑士团。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波兰后世的民族解放斗争有深远的影响。显克维奇在小说中通过描写各种人物受到骑士团残酷迫害的不幸命运,揭露了侵略者凶恶狡诈的本性,正是侵略者的压迫本性激起了波兰和立陶宛人民的反抗,他们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不证自明。显克维奇认为只有正义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取得最后的胜利。这部小说的出版不仅对于当时普鲁士占领者的民族压迫和波兰人的反压迫斗争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后来在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波兰期间,因为它对波兰爱国者和人民的鼓舞作用,德国法西斯把它列为禁书。
和显克维奇不同的是,波列斯瓦夫·普鲁斯(1847—1912)的小说大都是以波兰社会现实为题材。如他188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前哨》的故事就发生在普鲁士占领区的一个农村,占领者当局当时想要占领波兰的农村,主要采取大量移民的办法,妄图利用他们在经济上的雄厚实力控制这里的一切,然后对波兰农民采取同化政策,使波兰农村变成普鲁士的农村。可这一切遭到了波兰农民的极力抵制和反抗。小说主人公斯利马克是一个波兰的中农,德国移民要买他的土地和财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逼,但他没有屈服,始终坚守着波兰农村的这个前哨,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
普鲁斯在1887—188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玩偶》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一个华沙破落贵族子弟斯坦尼斯瓦夫·沃库尔斯基的社会经历,在广阔的背景上,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波兰王国特别是华沙的社会面貌。主人公沃库尔斯基年轻时是一个波兰的爱国者和革命者,曾在一个年长于他的友人热茨基的引导下参加过1863年的一月起义,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70年回华沙后,曾饱受饥饿的煎熬,但他1877年去了保加利亚,因为那里爆发俄土战争,他利用这个机会搞军需供应的买卖,挣得了几十万卢布的巨款,成了一个暴发户。回到华沙后,他便联合一些贵族,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对俄贸易公司,成了华沙商界的头面人物。普鲁斯在小说中,将其主人公描绘为一个19世纪下半叶波兰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沃库尔斯基善于洞察资本主义市场行情的变化,能够抓住机会,大胆进取,获得成功;在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上,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魄力,都远远胜过那些旧的贵族。沃库尔斯基做买卖也很讲诚信,这种诚信和关心消费者利益的经营方式,使得他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他也十分关心波兰的社会福利,常为穷苦的人排忧解难,还为十几个失业者安排了工作,为几百个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受到了他们的拥戴。
但在当时的波兰王国,虽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实证主义民主思想得以宣传,但封建贵族依然占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享有特权,主人公沃库尔斯基为了自己的发展,也不得不依靠这个阶层人物的支持,因此他曾极力和他们拉拢关系,并且还真心爱上了一个贵族小姐。这个贵族小姐的家庭已经败落,沃库尔斯基在她父亲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很多帮助。但是他后来发现,他爱的这个贵族小姐是个庸俗的女子,她表面上和他接触,是为了得到他对她父亲濒于破产家庭的支撑,可背后却和别的男人私通,还无耻地咒骂对她和她父亲有恩的沃库尔斯基,致使沃库尔斯基最后在绝望中自杀。他在自杀前,还将他的全部财产分送给了一些生活困难的穷苦人和那些他认为能够为波兰的复兴做大事的人。在普鲁斯笔下,沃库尔斯基是波兰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拥有巨额财产,虽然想和享有特权的贵族拉拢关系,但更多是为了波兰的复兴,为他眼中的穷苦人谋福利。普鲁斯十分看重像他笔下沃库尔斯基这样的人才,认为他如果不去接触那些腐朽没落的贵族,会为波兰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小说对波兰社会那些旧的封建贵族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这些人不事劳动,饱食终日,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去勾结波兰民族的敌人沙俄占领者的代表,置自己民族的危亡于不顾;但他们又自视高贵,看不起所有别的社会阶层的人。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波兰社会无法清除的毒瘤。小说的结尾笼罩着浓郁的悲观情绪,除了沃库尔斯基的自杀,那个曾经引导沃库尔斯基参加一月起义、之前还参加过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革命者热茨基也死了。还有一个在作者看来能为波兰的复兴干一番事业的人因为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也要到国外去。爱国主义作家普鲁斯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像显克维奇那样,表现出乐观向上和激昂慷慨的情调,但他的作品最真实、深刻地揭露了波兰现实的黑暗,所以他的小说《玩偶》一直被当作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著名女作家爱丽查·奥热什科娃(1841—1910)的作品也以波兰社会现实为题材,但更侧重于反映社会中妇女解放的问题。波兰旧的贵族为了显示他们的文明和高贵,他们的家庭成员爱讲法语,年轻女子要学会弹钢琴,但无须参加社会工作,因而都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和职业教育。奥热什科娃187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马尔达》描写的女主人公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她从小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作为一个贵族小姐,她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在父亲和丈夫相继去世后,她的家庭面临破产,而她自己又不具备从事某种社会职业的能力,因而无法单独谋生,最后走投无路进行盗窃,在警察的追捕下,跌倒在一条车轨上,被路过的马车轧死了。作品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揭露了封建贵族这个虚伪的陋习和当时社会的男女不平等。
长篇小说《涅曼河畔》(1887)是奥热什科娃的代表作,它以19世纪末立陶宛格罗德诺城涅曼河畔米涅维奇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通过爱国贵族别涅迪克特·柯尔钦斯基一家、少有土地的农民安哲里姆·包哈狄罗维奇和他的哥哥耶瑞以及耶瑞的儿子扬在1863年一月起义前后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波兰农村的社会面貌。别涅迪克特在一月起义期间,曾站在起义者的一边,起义失败后,他因受到沙俄占领者的横征暴敛和银行、高利贷者的敲诈勒索而面临破产。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拒绝了他的二哥多米尼克要他去俄国升官发财的建议,而坚守在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上。但作为一个封建贵族,为了挽救他家的危局,他对周围的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
别涅迪克特的大哥安德若依和他不一样,他一直对农民友善,同情他们的疾苦,他年轻时就和安哲里姆、耶瑞关系密切。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爱国贵族和农民一起参加起义斗争的场景,作者为起义的失败而悲痛,号召人们缅怀先烈,继承他们的遗志,去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别涅迪克特的儿子维托里德也曾用“人与人的平等和友爱”[10]的思想来劝导他父亲改变对农民错误的态度。但在作者看来,一月起义后的波兰社会中,真正能够继承起义的爱国和民主传统的,是受压迫最深的贫苦农民,作者把“祖国的复兴和强盛”[11]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奥热什科娃对小说人物的刻画,也以爱祖国、爱人民和爱劳动作为衡量他们的道德标准。在小说人物的画廊中,农民的形象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安哲里姆,他为人宽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仅在一月起义中经受过革命的洗礼,也是个劳动能手,既会种田,又会干木匠活,还是一个有经验的园艺家。耶瑞的儿子扬年轻时正值一月起义爆发,民族、家庭和他自己遭受的苦难他永远不会忘记,对沙俄占领者怀有深仇大恨。他生性淳朴、善良、正直,不仅具有熟练的劳动技能,而且有丰富的生产知识和较高的文化水平。但在贵族阶级中,有的人物经历曲折,如别涅迪克特有个外甥女尤斯青娜,她父亲达若茨基年轻时挥霍无度,贪图女色,母亲遭受的屈辱曾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她在父亲破产后来到了柯尔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受到这里的贵族亲友的歧视,因此对贵族的等级制度和腐化堕落充满了仇恨,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痛苦。这时候,她来到了扬的田庄里,感到只有在这个朴素但是“有朝气”的“新的世界”[12]中,才找到了真正的乐趣。后来她也愉快地参加了农田和麦收的劳动。在和扬的接触中,扬的爱国思想和他朴实、率真的品德和个性,以及他对她热情的关怀,使她对扬产生了炽热的爱情。因此她决心做一个她出身阶级的叛逆者,真正来到劳动人民中。她的叛逆行为在贵族阶级中曾引起过极大的震动,但她告诉舅舅别涅迪克特,扬“将把我领到他的贫穷的,然而是自己的家里,使我不仅可以得到快乐的生活,而且有可能运用我的双手和头脑帮助他从事劳动,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别人”[13]。这些话充分地表现了她崇高的精神风貌。尤斯青娜不仅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奥热什科娃的全部创作中,在波兰文学史上,都是闪耀着理想光辉的形象之一。奥热什科娃对于波兰社会的解放,特别是妇女解放的看法较她同时代的其他进步作家表现更深刻的地方在于,她不仅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各阶层的妇女都应从事劳动,自食其力,而不应不劳而获,社会也应当为她们创造适合从事某种劳动的客观条件。她号召妇女和传统所有制的一切陈腐观念作彻底的决裂,走向下层,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齐心协力地改造旧的社会。
玛丽娅·科诺普尼茨卡(1842—1910)是个诗人和作家,她写过一系列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1910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是其代表作。长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波兰农民由于缺少土地,在国内无法谋生,曾大批迁移到西欧、北美和南美,遭受了流落异乡的痛苦。长诗中所描写的农民来自波兰全国各地,因为感到自己在波兰已经没有生路,所以去巴西谋生,可这也是一条充满了艰险的路。首先,由于他们乘坐的船条件极为艰苦,许多小孩死于饥饿和疾病,尸体被抛入大海。侥幸活下来的人到达了巴西一个港口城市,他们曾住在这里的一个营棚里,后来到城里去,希望那里的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德国人,自称是那里的政府所派,要这些波兰农民登记入册,让他们服封建劳役,还要向他们征收赋税,这引起了波兰农民极大的不满,便愤然离开了这里另觅生路。他们穿过了一片大草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又有许多人死去。途中还遇见了一些从咖啡农场来的黑人,这些黑人比他们更穷,要和他们争夺食物,便和他们发生了打斗,双方死伤众多。
最后,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港口城市,高兴地看见这里居住着波兰侨民,于是来到侨民营里做客,却发现这些侨民已失去了本民族的习俗,孩子们连波兰话都不会讲了,港口工作也十分繁忙。有一次,农民们看见一条船上有人要拍卖一些口袋,里面装的是那些在船上饿死和病死之人的遗物,许多人争相购买这些便宜货。他们在一个口袋里还发现了一封死者临终前写给父母的信,信中表达了他对双亲和乡土的思念以及不能与亲人相见的痛苦。这些农民后来在港口的一个船坞里找到了工作,但这里气候炎热,劳动条件极为艰苦。有一天,港口举行罢工游行,波兰农民抬着一个饿死的同胞的尸体也参加了游行,他们把这当成是对当局的血泪控诉。尽管士兵挥舞军刀,对游行者进行威胁,他们也不害怕。
长诗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波兰农民在19世纪末被迫流亡国外的原因和他们在国外谋生的苦难经历。作品的最后一段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后所写的,诗人在波兰和俄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下,构思了一个港口工人罢工的场面,这不仅反映了19世纪末在俄国和波兰的民族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实情况,也表明了诗人坚决拥护革命的态度。另外,作品把波兰农民遇到的那些德国人描绘为当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并描写了他们对波兰农民的敲诈勒索,也表明作者对普鲁士占领者的仇视。
波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针对当时波兰遭受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占领者残酷的民族压迫下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全方位的解剖和分析,真实、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面貌,不仅充分表现了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精神,也为读者认识那个时代的波兰提供了真实的见证。
(原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1] 有人译为“艾丽查”,但笔者译为“爱丽查”。
[2] 引自艾丽查·奥热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林波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页。
[3] 以上均引自艾丽查·奥热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林波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页。
[4] 引自艾丽查·奥热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林波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0页。
[5] 引自艾丽查·奥热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林波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页。
[6] 引自艾丽查·奥热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林波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6页。
[7] 转引自阿利娜·诺菲尔《亨利克·显克维奇》,华沙,国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
[8] 见显克维奇《第三个女人》,林洪亮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552页。
[9] 见张振辉《显克维奇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10] 见艾丽查·奥若什科娃《涅曼河畔》,施友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页。
[11] 见艾丽查·奥若什科娃《涅曼河畔》,施友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页。
[12] 见艾丽查·奥若什科娃《涅曼河畔》,施友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
[13] 见艾丽查·奥若什科娃《涅曼河畔》,施友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