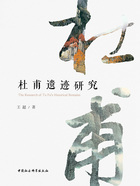
第二节 空翠堂的历代变迁
一 宋代兴建空翠堂
北宋宣和元年(1119)冬,张伋出任鄠县知县。张伋也是杜诗的忠实读者。他在《渼陂空翠堂记》中自述“昔时尝闻士大夫称关中多山水之胜,而渼陂在终南山下,气象清绝,为最佳处。及诵杜工部所赋诗行,爱其语大而奇,益欲一往游之,以慰所闻。道阻且长,斯愿未遂,每以为恨”。因此,担任鄠县知县之后,张伋便前往寻访渼陂之胜景,终于得偿多年夙愿。
此时的渼陂,与唐天宝年间杜甫来游之时并没有什么差别。张伋见渼陂“翠峰横前,修竹蔽岸,澄波浸空,上下一碧”,认为渼陂确实“气象清绝,为关中山水最佳处也”。渼陂北岸“有堂旧矣,久弗加葺,栋宇倾挠,来游者阽压是惧”。张伋感到非常奇怪,“有此佳山水,而堂构不修,宴赏无所,大非其宜”。询问身边从吏后“乃知自清平建军县,涝水之西割地以隶,故陂虽近鄠,而地非所属。虽属终南,而距邑为远。远者不喜修,近者不得修,岁月既久,浸成弊坏,瓦木之类,至为小人攘窃而莫之问,可不惜哉!”[9]张伋所说的“清平建军县” “终南”是指清平军与终南县,据《宋史》记载:“清平军。本凤翔府盩厔县清平镇。大观元年(1107),升为军,复置终南县,隶京兆府。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专管勾上清太平宫。县一:终南。”[10]盩厔县清平镇于北宋大观元年升为清平军,并新设终南县。与鄠县以涝水为界,涝水以西属清平军,以东为鄠县。渼陂北岸虽然地近鄠县,但却属于清平军终南县辖地,又因为该堂距离终南县远,所以出现了“远者不喜修,近者不得修”的尴尬局面,最终导致该建筑损毁。
张伋则力主修复该建筑,又于宣和四年(1122)二月寒食节,约请“联事诸公会于陂上”,“因相与为议曰:‘渼陂之地虽在他邑,而顷者漕台移檄,尝令吾邑就近管辖。此堂不修,无罪邻邑,亦吾邑之过也。吾属到官日久,行且受代,后来君子,谓如不好事,何今欲缮完,稍加宏壮,使称是山水之胜,且以待使者。按部之经由备邑人岁时之游乐,可乎?'”以陕西路都转运使司(漕台)曾令鄠县就近管辖渼陂之官方文书为号召,期望大家共襄盛举,恢复陂北之堂。该提议得到了联事诸公的赞同。署理清平军事吴景温是张伋的旧相识,得知此消息也命本地工匠与鄠县工匠配合施工。“于是增卑补薄,基趾廓焉;去故取新,栋宇壮焉。前驾虚阁,以临清流;后辟轩窗,以快雄风。规度适中,不僭不陋,气象具存。苟完苟美,经营于二月之晦,断手于五月之朔。”新堂建成之后,张伋非常满意,“升堂远望,豁达无碍,南山之秀,陂水之广,举目可尽”。又于五月初五宴于该堂,是日“小雨乍收,微风四起,岚光水气,相为氤氲,若烟之浮,若露之润,有见于帘楹轩槛间者,明灭变态不一而止,是何清且丽邪”,众人皆以为该天气景色皆是杜甫《渼陂行》诗中语,“咸请以‘空翠’名其堂”[11]。渼陂空翠堂由此得名。
二 明代重建空翠堂
自北宋宣和四年,鄠县知县张伋于渼陂北岸兴建空翠堂之后,该堂作为渼陂周围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一直得到较好的保护与维修。但到了元代,当地人“以渼陂之鱼能治漏,因决陂取鱼,陂之亡也”[12]。
明“嘉靖间,御史方公新以使事过鄠,命知县王玮创修堂三楹、厨三楹,莲池一区,仍栽竹种树,前有紫阁,后又菱池,气象清幽,松竹丛中,水磨之声不绝”[13]。“御史方公新”即方新,时任巡茶御史。明万历《陕西通志》“巡茶御史察院”载:“方新,直隶青阳人。进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14]隆庆元年(1567)二月,鄠县知县王玮重刻张伋《渼陂空翠堂记》,立于空翠堂[15]。由方新到任时间与王玮立碑时间推测,重建空翠堂之事当在明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元年之间。
明崇祯十二年(1639)春,时值明末,陕西关中一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寇警”不绝。鄠县知县张宗孟稍得空闲,寻访渼陂故址,此时渼陂已干涸三百余年。“水落土出,尽为稻垄,惟渼水无恙,仅留陂之一字,与渼水共存焉耳”,空翠堂故址尚在,“亦倾圮莫识”。张宗孟此行并非全为寻古访幽,而是此前听说“城西三里为陂头镇,有高阜,上为空翠堂。按其地可拒寇,因建堡浚壕”。作为地方父母官,张宗孟也有顺带查看军事堡垒的意图。
张宗孟在空翠堂遗址见到了张伋所作碑刻,感慨“向之裁霞襚彩,因风回荡,菁葱掩映,百羽萃止,啁啾美喧者,杳然无存矣”,甚为惋惜,“因鸠工庀材,相形度势,移堡后古道于北百步外,而高大之,则渼陂当年所决处也。为桥以通往来,桥北建武曲庙镇之。堡东建书院,楼房三楹,东西号房各三楹。又东旧有文昌庙,亦更新之。环浚鱼池阔五丈,与堡壕通,鲭鲤鳣鲔,杂畜其中,置小船以利涉,而资钓间。植桃李梅杏、榆柳松桧之属。数年后,松涛篁韵,相映参差,不恍然旧胜之犹存乎?堡前造水磨一所,从堡内居民之便,且引水入壕,作金汤之险,则又不独选胜寻芳之是亟也”[16]。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空翠堂异地重建,仅保留其名而已,张宗孟的真实意图则在于强陂头镇所建堡垒的军事防御力量。
社会动荡,明王朝的命运朝不保夕,作为地方官员的张宗孟也有着切身体会,心中不免有几分伤感,他说:“余惟杜公之迹以渼陂存,非渼陂借本公以存也。杜公诗行称最于唐,兴致亦不浅,所游辄纪其迹。唐之后为宋,而空翠堂之创,又为宋张令,其时陂犹未决。至昭代,则陂决于元,并空翠堂亦寥落就圮矣。渼水潆洄,亘千古而常碧。昔大历、会昌中,平泉绿野,奇峰之石,履道之竹甲天下,其团园主人矢曰:‘后世有鬻平泉一片石,即为不类。’然迄今亦杳不可问矣。余宁必是役之不朽万世哉。”[17]杜甫之行迹因游渼陂而存留于诗中,而渼陂并没有因为杜诗的存在而永远存在下去。渼水虽然,但渼陂早已无处寻觅,加之“寇警”频仍,张宗孟内心的焦灼与寥落已不是诵读杜诗与重建空翠堂所能抚慰的了。大有景物无踪、人生无常的末世之伤感。
三 清代兴建杜公祠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春,陕西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驿传道贾鉝“巡驿关中,过鄠邑,观渼陂,俛仰流连,犹想见公(杜甫)当时游息之地,与岑家兄弟赋诗凭吊之概,低回徘徊久之,深悼公之遇,惜其才,高其志,而窃谓其胜迹不可以终湮也”,遂与鄠县知县朱文卿商议兴建杜公祠,朱君“亦风雅士也,欣然有共襄之志。余乃捐俸为之。构堂数楹,祀公其中。朱君实经理之,余仍属以时荐蘋藻焉”[18],并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望日”作《渼陂唐杜工部祠堂记》以记其事[19]。
鄠县知县朱文卿也作有《渼陂创建杜工部祠记》一篇。文章开篇即谈及于渼陂为杜甫创建祠堂的原因。“自古有大功德于其地,以及名贤、硕儒、忠臣、孝子、节妇、义夫,足为百代矜式者,乡邑咸祠而祀之,以劝将来。先生当唐天宝之乱,位不过卑散,间关数千里,奔赴行在。至其平时,则触时感事,忧国爱君之义辄形楮墨,一腔忠愤,皎皎乎盟日月而泣鬼神。故其足迹所至,后之人往往追念余芳,建祠刻诗。”[20]由此可见,杜甫忠君爱国、满腔忠义,显然属于名贤、硕儒、忠臣之列,且在鄠县渼陂留下过重要诗篇,功德自不待言。
此时,明朝末年知县张宗孟移建的空翠堂已成废址,朱文卿便依其故址“构堂以祀”。“庶几远山拱翠,碧水呈波,如睹先生丰采焉;鸣泉水硙,松韵竹声,如闻先生啸歌焉。以表前贤,则芳徽不坠;以风后世,则劝善有型。视世之敝,所事以事,无益糜有用之财,以媚不经之鬼者,得失不有间哉!”建立祠堂既在于表彰前贤,亦在于宣扬鄠县地方风物景观。
渼陂杜公祠“为台五尺,为堂三楹,外缭以垣,涂之白垩也。正前为门,外为坊,共费钱凡百二十余贯”。不过根据清雍正《鄠县重续志》的记载,渼陂杜公祠与空翠堂实为一体。“空翠堂,建自宋之张公伋。与渼陂书院东西连接,堂后有阁,堂前兼有廊厢、门坊。日久就废,康熙庚寅秋,观察河东贾公(鉝)、前令怀来朱(文卿)捐俸建新堂于旧堂之南”[21],此处只说贾、朱二人重建空翠堂事,而不载创建杜公祠事。但根据贾鉝、朱文卿所述可知所建当为杜工部祠。两相比较可知,二人创建杜公祠的同时,仍于祠外张挂了“空翠堂”牌匾。
鄠县儒学教谕李滋于雍正九年(辛亥,1731)秋,游览渼陂,见空翠堂有倾圮之虞,又与众弟子员捐资重修空翠堂,并新建崇文阁。李滋在《重修渼陂空翠堂并建崇文阁碑记》中追述空翠堂的创建历程,记云:
前张侯(伋)创之于地隶清平之日者,非好事也,惧名胜之易湮,怅前徽之忽泯,而贻后人以俗吏不好古之诮也。后张侯(宗孟)修之于兵戈抢攘之秋者,非劳民也,思以绍胜迹于既往,垂成规于将来,求不负乎修废举坠之职也。至贾公则论世知人、俯仰上下,慨然有显微阐幽之思焉。朱侯则景贤崇正,深情遥致,卓然有型俗维风之意焉。是皆可为居官莅政者之式矣。然迄今空翠之堂长留于渼陂之上,而诸公之名亦遂与杜公之贤并存于斯堂而不朽。[22]
李滋文中将空翠堂与纪念杜甫并提,也可见空翠堂与杜公祠本就是同一座建筑。空翠堂此后一直保存良好。民国《续陕西通志稿》载:“杜工部祠,在渼陂。康熙中重修,贾观察[鈜](鉝)、邑令朱文卿均有《记》,见邑志。观察捐俸四十金,又手题匾联,悬檐楹,书片石置诸壁间。”[23]现存古建筑为清末重修,殿堂两座,共六间,堂前仍保存明清以来碑刻七方。1957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唐)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一《古诗五十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2](唐)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卷三《五言律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1—472页。
[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京兆府下·鄠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4]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卷一七《说林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93页。
[5](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京兆府下·鄠县》,第31页。
[6](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一五《县五·鄠县》,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页。
[7]《杜甫集校注》卷一《古诗五十首》,第126—127页。
[8](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124页。
[9](清)康如琏修,康弘祥纂:康熙《鄠县志》卷一二《文苑考·记》,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125—126页。
[10](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七《地理三·陕西·永兴军路》,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46页。
[11](清)康如琏修,康弘祥纂:康熙《鄠县志》卷一二《文苑考·记》,《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126—127页。
[12](明)张宗孟:《重建渼陂记》,康熙《鄠县志》卷一二《文苑考·记》,《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169页。
[13](清)康如琏修,康弘祥纂:康熙《鄠县志》卷三《古迹考》,《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册,第402页。
[14](明)李思孝修,冯从吾等纂:万历《陕西通志》卷一二《公署·巡茶御史察院》,第2册,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影印明万历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15]按,该碑仍存,今在鄠邑区玉蝉乡陂头村空翠堂院内。额文篆书“空翠堂记”,碑文作者题名“宋宣教郎知京兆府鄠县管勾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张伋撰”,落款题为“明隆庆元年春二月吉日。知鄠县事冀石王玮重立”。刘兆鹤、吴敏霞编著:《户县碑刻》著录石刻拓片及录文(图,第82页;录文,第366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16](明)张宗孟:《重建渼陂记》,康熙《鄠县志》卷一二《文苑考·记》,《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169—170页。
[17](明)张宗孟:《重建渼陂记》,康熙《鄠县志》卷一二《文苑考·记》,《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170—171页。
[18](清)贾鉝:《渼陂唐杜工部祠堂记》,(清)鲁一佐修,周梦熊纂:雍正《鄠县重续志》卷五《新增艺文·碑文》,清雍正十年刻本,《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505—506页。
[19]按,雍正《陕西通志》卷二三《职官四》“驿盐道”载:“贾鉝,镶蓝旗汉军。康熙三十八年任。”(《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1辑,第2册,第85页)“驿盐道”即“分巡驿盐道”属陕西提刑按察使司下辖,“旧为驿传道。康熙二十一年裁,事务悉归粮道。三十三年复设。雍正十二年并入盐务,改为驿盐道”(第79页),由此可知贾鉝时任分巡驿传道。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存有贾鉝所绘《太白全图》《太华全图》《香节图》等三方线画石碑,其中《太白全图》落款题为“时康熙三十九年中秋三亲观察使河东贾鉝并识”(参见《西安碑林全集》第104卷《石刻线画》,第315—323页),与此文作于同一时期。
[20](清)朱文卿:《渼陂创建杜工部祠堂记》,雍正《鄠县重续志》卷五《新增艺文·碑文》,《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506—507页。
[21](清)鲁一佐修,周梦熊纂:雍正《鄠县重续志》卷五《建置·改创》,《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266—267页。
[22](清)李滋:《重修渼陂空翠堂并建崇文阁碑记》,雍正《鄠县重续志》卷五《新增艺文·碑文》,《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册,第509—510页。
[23]杨虎城修,宋伯鲁纂: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一二四《祠祀一》,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