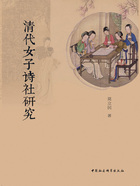
绪论 诗社、女子诗社界定与清代女子诗社演进历程概说
“社”者,其最早的意义是指掌管土地的土神。先秦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后土为社。”[1]《礼记外传》:“社者,五土之神也。”[2]后来“社”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团体或地方基层组织。作为民间社会团体,“社”的功能既可用之于祭祀神灵、先祖等活动,也可用之于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动员、组织工作。《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3]《国语·鲁语上》:“故祀以为社。”[4]又《梦粱录》卷十九“社会”:“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5]作为地方基层组织,中国古代的“社”相当于我国当代社会乡村与城市社区管理最基层的单位,其功能主要是理民助民。《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6]清人顾炎武:“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7]
诗社是指诗人或诗歌爱好者定期或不定期聚会而组构的文学社团,他们以此为纽带,或赋诗吟咏,或切磋诗艺。北宋马令《南唐书·儒者·孙鲂》:“孙鲂,字伯鱼,性聪敏,好学。唐末,都官员外郎郑谷避乱江淮,鲂从之游,故其所吟诗,颇有郑体。及吴武王据有江淮,文雅之士骈集,遂与沈彬、李建勋为诗社。”[8]明朝李东阳《麓堂诗话》:“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9]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务结二三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10]
中国古代的诗社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诗社是一种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的文学团体,它没有诗社社名,也没有诗社章程与规约,而是一群志趣趋同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聚合在一起,通过诗歌创作,以吟风弄月、状情言志,同时也有把酒弄盏的生活情趣。这类诗社大多是文士或闺秀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的诗歌雅集唱和与酬答活动,尽管没有诗社之名,但行诗社之实。狭义诗社则组织结构比较严格,它有正式诗社社名,定期或不时进行诗歌创作活动,有比较稳定的诗社成员与活动地点,也有诗社主盟人,部分狭义诗社还订有诗社章程与规约。如北宋文彦博主持的洛阳耆英会,明代嘉靖年间的西湖八社,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北京宣南诗社以及《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等人组织的“海棠社”“桃花社”就是这样的诗社。本书所研究的清代女子诗社,兼收并蓄,兼及“广义”与“狭义”两大类。
我国古代诗社最早出现在初唐。诗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担任司户参军时曾在当地组织“相山诗社”。明余之祯万历《吉安府志》卷十二载:“相山,在城隍岗,山一名西原,平衍幽旷,步入即有林壑思致。唐杜审言司户吉州,尝置相山诗社。”同书同卷又云:“诗人堂,在西原能仁寺侧,唐司户杜审言结诗社于此。”[11]康熙《江西通志》卷之第七云:“相山在府城西,即西原山,平衍幽旷。唐杜审言司户吉州,结相山诗社。宋周必大罢相归,与故旧憩息于此,构司户祠。明陈嘉谟辈置西原会馆,买田以膳来学之士,今废”。[12]杜审言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进士,年轻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他是初唐唐高宗与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延及两宋时期,文人结社风习兴盛,诗社、词社等文学组织得以蓬勃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文人结社运动的第一波高潮。欧阳光论两宋文人诗歌结社运动之盛时说:“有宋一代,文人结社唱和活动十分活跃,各种类型的诗社文会蓬勃兴起,遍布域中。据笔者初步考察,有材料记载的各类诗社达六七十家,较为著名的如邹浩颍川诗社、徐俯豫章诗社、贺铸彭城诗社、叶梦得许昌诗社、欧阳彻红村诗社、王十朋楚东诗社、乐备昆山诗社以及西湖诗社等。”[13]而据陈小辉博士学位论文《宋代诗社研究》统计,得北宋诗社93家,南宋诗社144家,两宋共得诗社237家。
最早严格意义上的诗社当从北宋神宗与哲宗元丰、元祐年间贺铸彭城诗社和邹浩颍川诗社算起。我们说的严格意义的诗社即上文所说的狭义的诗社。这类诗社有比较固定的诗社成员,不时或定期举行诗歌创作活动,一般还有诗社社名。贺铸在《田园乐》诗中小序中曾讲到“彭城诗社”的诗歌唱和活动。此诗小序说:“甲子八月,与彭城诗社诸君会南台佛祠,望田亩秋成,农有喜色,诵王摩诘田园乐,因分韵拟之。予得‘村’字。”[14]另一首《读李益诗》小序也说:“甲子夏,与彭城诗社诸君分阅唐诸家诗,采其平生,人赋一章,以姓为韵。”[15]彭城诗社不仅诗歌唱和活动比较频繁,而且社中成员比较固定,诗社主要成员有张仲连、陈师中、王适、寇昌朝、王文举等人。贺铸《彭城三咏》诗小序说:“元丰甲子(1084),予与彭城张仲连谋父、东莱寇昌朝元弼、彭城陈师中传道、临城王适子立、宋城王 文举,采徐方陈迹分咏之。予得‘戏马台’、‘斩蛇泽’、‘歌风台’三题,即赋焉。”[16]又贺铸《渔歌》诗小序:“甲子十二月,张谋父、陈传道、王子立,会于彭城东禅佛祠,分渔、樵、农、牧四题以代酒令,予赋渔歌。”[17]其《三月二十日游南台》诗小序:“与陈传道、张谋父、王文举乙丑年(1085)同赋,互取姓为韵,予得‘陈’字”。[18]
文举,采徐方陈迹分咏之。予得‘戏马台’、‘斩蛇泽’、‘歌风台’三题,即赋焉。”[16]又贺铸《渔歌》诗小序:“甲子十二月,张谋父、陈传道、王子立,会于彭城东禅佛祠,分渔、樵、农、牧四题以代酒令,予赋渔歌。”[17]其《三月二十日游南台》诗小序:“与陈传道、张谋父、王文举乙丑年(1085)同赋,互取姓为韵,予得‘陈’字”。[18]
邹浩颍川诗社也是一个组织比较规范的诗社,其《颍川诗集叙》讲述了颍川诗社结社的经过与社中的诗歌创作活动。《颍川诗集叙》云:“故人苏世美佐颍川幕府,既阅岁,余始承乏泮宫,与世美皆江都尉田承君友。承君知其为僚于此也,书来告曰:‘韩城吾里,崔德符、陈叔易天下士也。东南豪英森,号为儒海,吾尝默求二子比者,殆不与耳接,子其亲灸之。’叔易方杜门著书不外交,德符久之,始幡然命驾。时裴仲孺、胥述之里居久矣,文行籍籍在人口,亦喜德符为我辈来也,而与盟焉。”又云:“叔易虽未及致,而并得二士又过望。非公家事挽人,则深衣藜杖,还相宾主,间或浮清,款招提,谈经议史,揖古人于千百岁之上,有物感之,情与言会,落于毫楮,先后倡酬,以是弥年,裕如也。世美秩满且行矣,用刘白故事,裒所谓倡酬者与自为之者、与非同盟而尝与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颍川集》。”[19]
中国古代诗社还有若干别称,或称吟社。《群雅集》记载清代著名诗人江干结社活动说:“片石(江干字片石)偃蹇海上,苦吟度日。其诗 削故轨,标领新情,雉水之秀也。与徐荔村、冒芥原、仲松岚、宗杏原、陈小山、徐弁江、吴梅原、冒柏铭结‘香山吟社’。荔村有‘九人共结香山社,十万欢场到白头’之句,风流令人可羡。”[20]或称诗会、吟会。《国朝松陵诗征》记载清代诗人孙元诗学活动说:“也山(孙元字也山)与沈餐琅、顾玉洲辈结‘岁寒诗会’,一时传为盛事。”[21]又称诗课、吟课。《江苏诗征》记述清代诗人宫国苞诗学结社经历说:“上舍(宫国苞字上舍)工诗善画。州人仲云江、叶古轩、邹耳山、罗夏园结‘芸香吟课’,上舍司月旦者十余年。”[22]有时也称“吟榭”。查揆《筼谷文钞·“东山诗榭”序》:“乾隆辛亥、壬子之间,予方弱冠,与少白陆先生、家茂才世官结吟榭于龙山之麓。冯茂才念祖、吴孝廉衡照、舍弟奕庆与焉。”[23]
削故轨,标领新情,雉水之秀也。与徐荔村、冒芥原、仲松岚、宗杏原、陈小山、徐弁江、吴梅原、冒柏铭结‘香山吟社’。荔村有‘九人共结香山社,十万欢场到白头’之句,风流令人可羡。”[20]或称诗会、吟会。《国朝松陵诗征》记载清代诗人孙元诗学活动说:“也山(孙元字也山)与沈餐琅、顾玉洲辈结‘岁寒诗会’,一时传为盛事。”[21]又称诗课、吟课。《江苏诗征》记述清代诗人宫国苞诗学结社经历说:“上舍(宫国苞字上舍)工诗善画。州人仲云江、叶古轩、邹耳山、罗夏园结‘芸香吟课’,上舍司月旦者十余年。”[22]有时也称“吟榭”。查揆《筼谷文钞·“东山诗榭”序》:“乾隆辛亥、壬子之间,予方弱冠,与少白陆先生、家茂才世官结吟榭于龙山之麓。冯茂才念祖、吴孝廉衡照、舍弟奕庆与焉。”[23]
中国古代女子诗社起步较晚,它起始于晚明,兴盛于清代。中国古代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女子诗社即为晚明“名媛诗社”。“名媛诗社”以晚明安徽桐城望族方以智家族中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三姐妹为核心,外加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吴令则,她们不时在方维仪的“清芬阁”中吟诗填词,互相唱和,以此形成中国古代最早的女子诗社。逮至明末清初以及盛清与晚清,众多的女诗人纷纷结社吟诗,大大小小的女子诗社得以在清代蓬勃发展,成为清代诗歌创作重要的构建元素,中国古代女子诗歌结社活动由此呈现繁荣昌盛的巅峰景观。
从清代女子诗歌总集、别集、诸多清代方志以及清代闺秀诗话、词话等研究文献考索,本书共统计出近30个对清代女子诗坛具有全局或地域性影响的重要女子诗社。这些女子诗社虽然不是清代女子诗社的全部,但占据了这一领域的主体部分,能够展现清代女子诗社的生存格局与基本风貌。从这些女子诗社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规律来探析,我们可以发现,清代女子诗社数量众多,社群质素完备,发展平稳而繁荣,没有大起伏。清初和盛清女子诗社大多以血亲与姻亲为纽带聚合而成,可称其“亲缘构建”的时代;晚清因师友交往而组合的女子诗社后来居上,可称其“师友集成”的时代。可以说,历史传统与时代语境是清代女子诗社赖以成长的温床,亲缘与师友则是直接促成其兴盛的催化剂。
所谓“亲缘构建”的时代,是指从清初顺治到清代中叶乾、嘉时期170多年的时间里,清代女子诗坛虽然崛起一些师友型诗社或亲缘、师友兼而有之的综合型诗社,如清初康熙年间著名的“蕉园诗社”、盛清乾隆年间著名的“清溪吟社”等,但其占绝对多数者则是以血亲与姻亲两大家族元素构建而成的家族女子诗社,如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祁氏女子社、清初松江(今属上海市区)章氏六女社、清初吴门(今苏州市)张氏七女社、盛清归安织云楼女子社、盛清建安荔乡九女社、盛清镇江鲍氏三姊妹社等。这些女子诗社的成员,要么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内的母女、姐妹、姑侄,她们热心诗词创作,以此组合成一个纯血亲型女子诗社;要么以一家一姓的血亲关系为主干,以婚姻网络为枝丫,或母女婆媳,或姊妹妯娌,或小姑大嫂聚合在一起,吟诗创作,彼此唱和,构建成一种血缘姻亲兼而有之的混合型家族女子诗社。这两类女子诗社的女诗人在结社过程中绝大部分没有自觉的群体组合意识,而是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不自觉之间自然地走到一起。如果说血缘姻亲是这类诗社得以组合的必要基础,那么共同的文学“兴趣缘”则是她们得以组合成社的直接原因。
所谓“师友集成”的时代,是指从晚清道光朝到民国成立90多年的时间里,清代女子诗坛虽然仍然存在许多以血亲或血亲姻亲为基础构建而成的家族女子诗社,但以师友为网络组构而成的新型女子诗社则得以不断崛起,其数量与质量可与同期血亲姻亲型家族女子诗社相颃颉,它们为清代女子诗坛带来若干诗学新元素与新气象。晚清师友型女子诗社的组构成员绝大多数为闺秀诗人彼此之间的闺阁友人,也有少量为同性上辈尊长。如晚清以沈善宝与顾春为核心的“秋红吟社”,晚清以沈珂为代表的江西会昌“湘吟社”,晚清以谢漱馨为代表的江西宜黄“晚香诗社”等。一般而言,参加这类诗社的女诗人,大多有自觉的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她们往往以一两位女诗人为核心,团聚在一起,互相唱和,切磋诗艺,由此形成一种在组织上比较严密与规范的女子诗社。
总之,清代女子诗社数量众多,社事活动丰富多彩,优秀诗人蔚起群出。尤其精彩的是,清代女子诗社诗学与社团元素饱满,诗性棱角鲜明,演进历程清晰可辨,不惟丰富了我国古代诗社的诗学内容与文化品格,亦促进了清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它是我国古代诗社与清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时性演进与共时性生存来考察,清代堪称我国古代女子诗社演进最为灿烂辉煌的“巅峰”时期。
[1](先秦)左丘明:《左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
[2](唐)成伯玙:《礼记外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104页。
[3](先秦)《尚书·甘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尚书》未标注作者。
[4](先秦)左丘明:《国语·鲁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5](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6](清)惠士奇:《礼》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37页。
[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2,康熙三十四年(1695)遂初堂刻本,第16页。
[8](宋)马令:《南唐书》卷13,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汝达刻本,第6页。
[9](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页。
[10](清)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45页。
[11](明)余之祯:《吉安府志》卷12,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本,第176页。
[12](清)于成龙:《江西通志》卷7,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第13a页。
[13]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14]傅璇琮、孙钦善:《全宋诗》第1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20—12521页。
[15]傅璇琮、孙钦善:《全宋诗》第1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20页。
[16]傅璇琮、孙钦善:《全宋诗》第1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98页。
[17]傅璇琮、孙钦善:《全宋诗》第1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99页。
[18]傅璇琮、孙钦善:《全宋诗》第1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21页。
[1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28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20](清)王豫:《群雅集》卷10,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第6a页。
[21](清)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卷15,乾隆三十二年(1767)爱吟堂刻本,第8a页。
[22](清)王豫:《江苏诗征》卷1,道光元年(1821)刻本,第15a页。
[23](清)查揆:《筼谷文钞》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