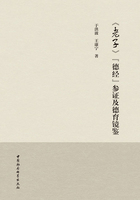
第2章 《老子》的“道”与“德”
《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全书分为“上篇”和“下篇”,或曰“上经”和“下经”,又曰“道经”和“德经”。《老子》的“道经”详于“道”,“德经”则详于“德”。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对《老子》“德经”各章的内涵进行解读,进而对道德修养等相关问题予以参悟。由于老子之“德”源自于“道”,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故而本章拟对二者的渊源、主旨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予以简单梳理。由于有关《老子》“道”与“德”的先行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下文仅择其要者及有心得处予以简单分析。
任何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大凡都有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构成;而本体论或曰宇宙观,又是后两者的前提。抑或说,哲学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是由本体论引申而成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究的核心问题大致包括: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宇宙的衍生及其本质是什么,人自身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支终极问题。由此可见,哲学的本体论,可谓整个哲学体系的“元知识”。作为探究“元知识”的哲学本体论,必然要追问天地人乃至于宇宙万物的渊源及其本质等本原和终极问题。在功利主义和快餐文化风靡于世的今天,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终极问题,似乎业已成为现代人不屑一顾的悠悠往事。实则,对这些终极问题的追问,应该被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或许,正是对这些看似“无所为而为之”问题的追问,方有人类本身的发展及其文明的进步。
胡适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时,毅然打破之前从夏商周三代或从“五经”开讲哲学的传统,直接从《老子》开始讲起。胡适之所以敢于冒如此“离经叛道”之大不韪,大凡在于其认为,尽管在《老子》之前有诸多关于“帝”“天”“道”和“德”等与形而上学有关的典籍,但是其零散的论述尚不足以构成系统的哲学本体论。抑或说,唯有《老子》之“道”与“德”,方堪称之为系统的哲学本体论。
举凡人类,都有“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的天然好奇心。所谓“知其然”,即是“知”事物(西哲通常称“事物”为“存在”)之“然”;所谓“知其所以然”者,即是知“然”之“所以”。正是在追问“然”和“所以然”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获得了在天地之间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常识”。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常识”,大凡皆来自于感官可及的“存在”,即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这些由人类感官可及的“存在”归纳而成的“常识”,通常被称之为“形下之学”。正如《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所谓“形而下者”,即人类感官可及的“存在”;所谓“形而上者”,即人类感官不可及的“存在”。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对“可见”的“形下之器”知其“然”之后,似乎还始终保有对“不可见”的“形上之道”穷究其“所以然”的好奇心。可以说,正是对“形上之道”之“所以然”的不断追问及其形成的终极回答,才形成了古今中外诸多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也正是这些被看作是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类社会终极规律的认识成果,一直在引领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老子》之“道”,大凡即属于此。
如上文所及,夏商周三代大凡皆信奉神秘化的“帝”或人格化“天”为世间万物和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使自身的行为符合至高无上的权威之“天”,三代皆奉行“以德配天”的人间社会准则。“以德配天”的准则落实到人间,即是“礼乐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礼乐文化”。老子要“突破”三代所沿袭的权威之“天”,就必然要建构一个高于“天”的终极权威——此乃《老子》之“道”。
在“突破”三代沿袭的权威之“天”时,《老子》之“道”的权威性必须要远高于“天”。吊诡的是,《老子》之“道”的权威性,并非依仗于自身天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恰恰来自于“道”对自身权威性的消解,如其所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和“为道日损”等,大凡即属于此。抑或说,老子通过赋予“道”以“无为”和“自然”的本性,从而消解了“道”自身对于其所生人间万物的权威性。抑或说,正是基于“道”的“无为”和“自然”的固有本性,由“道”所生的世间万物乃至于人类,方能藉于自身得之于“道”的“自然”天性而得以自由地发展并最终自成其是。关于“道”的“无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另拟一章予以具体分析,此不赘述。
正如《周易》所谓的“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老子之“道”的首要功能和特点,亦在于其“生生之谓道”。“道”的“生生”及“生万物”的过程,集中体现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句。对于此句中的“一二三”,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下文拟结合《周易》中的“太极”和“两仪”等概念对之予以解读。
尽管《老子》“五千言”无一字言及“易”,但是老子却深得“易”之精髓。学术界素有“易乃六经之首”之谓,老学界亦有“不知易,无以解老”之谓。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句,著名学者奚侗认为,“道与易,易名而同体。此云一,即太极;二,即两仪,谓天地也;天地气合而生和,二生三也。和气合而生物,三生万物也。”奚侗之解,其依据当来自于《易传·系辞上》之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根据奚侗之解,“易”即是“道”;“太极”即是“一”;“两仪”或曰“天地”,即是“二”;“天地之气合和”即生“三”;“和气合”而不辍,即“生万物”。
具体而言,“道生一”中的“一”与“易有太极”中的“太极”相同。《易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两仪”即“阴阳”。众所周知,太极图由一黑一白两条阴阳鱼构成。纯黑色的鱼表示阴,但其中有一白点,表示黑鱼的眼睛;纯白色的鱼表示阳,但其中亦有一点黑,表示白鱼的眼睛。这意味着,“阴”本身自有一点“阳”,而“阳”本身亦自有一点“阴”。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中亦自含“阴”与“阳”。同样,在“道生一”的“一”中,亦自含“阴”与“阳”。由于“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只有“阴阳”相交合和,乃生新物;此新物即是“三”,亦即老子所谓的“二生三”。老子所谓的“二”或曰“阴阳”,又可谓之为“天地”或“乾坤”。在《周易》八卦中,“乾坤”两卦通常被称之为“父母卦”,以其长于“生生”是也,“生生之谓易”是也。正如《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化合,乃生万物;此与老子所谓“三生万物”几近相同。所谓“三生万物”,乃“三”复相交不已,亦复生生不已,故而“万物”生矣,生机盎然之宇宙存矣。
作为中华文明源头之典范的《周易》,之所以被称为“六经之首”,大凡在于其对宇宙万物乃至于人间之道业已了如指掌。故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通过作《十翼》而深得易之义理。《周易》的精髓,大凡在于其业已彻透宇宙万物皆具“阴阳”两种特性,万物乃至于人类社会的兴衰交替,皆由“阴”与“阳”之间的相互消长合和所致。“阳”与“阴”推及于大自然,即为“天”与“地”;画符于八卦,即为“乾卦”与“坤卦”。孔子主要继承了《周易》的“乾卦”之“阳刚”,而老子则主要承继了《周易》的“坤卦”之“阴柔”。正如《周易·象传》所谓的“乾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宗“阳”法“乾”的儒家,力倡“自强不息”的积极“有为”;而宗“阴”法“坤”的道家,则主守“厚德载物”而“无为”。此后,道家和儒家形成了一柔一刚的性格特征;二者相合,则刚柔并济,二者相分,则此消彼长。二者的消长合和,对其后的文化与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何以能够“生一”进而“生万物”?老子的回答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甚或是“有无相生”。此处的“万物生于有”易于理解,但是“有生于无”和“有无相生”却几乎超出常人的想象。或许,老子所举具体事物的“有无”及其“用”,较利于人们的理解。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作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官,老子认为,人类历史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人们贪得无厌于“器用”之“有”,却抛弃了最根本的“道体”之“无”。关于历史教训中的“有”与“无”,常人也可以经由反省而知晓。最难以理解者,或许是本体论或逻辑意义上的“有生于无”和“有无相生”。
可以说,对“无”这一概念的发现,进而对“无为”“无名”“无欲”“无事”等相关问题的系统阐发,可谓老子哲学的一大创举。实际上,老子所谓的“无”,并非纯粹的“空无”“虚无”“真无”或“不存在”。笔者认为,老子之“无”,可以理解为在“道”中与“有”互为对待、势能交换、相互转化的“同体存在”和“共时存在”。老子所谓“有生于无”中的“有”,亦并非可见的具体事物之“有”或时间上的“先无后有”的“有”,而是在“道”中与“无”互为对待、势能交换、相互转化的“同体存在”和“共时存在”,是二者缺一不可的存在。易言之,“有”与“无”的区别,不是“可见如否”的“存在”与“不存在”,也不是“时间先后”的“存在”与“不存在”,而是在“道”中“互为存在”的区别。
正如《周易》之所言“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之“道”中的“有”和“无”,可视为《周易》中的“阴”和“阳”。由此而言,亦可谓之曰“一‘有’一‘无’谓之道”,或“一‘无’一‘有’谓之道”。由此而言,“生生之谓易”,亦可换言为“生生之谓‘道’”。正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易”之所以成为“易”,皆赖于“一阴一阳”的“同体存在”,及其二者的相互合和乃至于“生生”。同样,亦可谓“孤‘有’不生,孤‘无’不长”,“道”之所以称之为“道”,皆赖于“一有一无”的“同体存在”和“共时存在”,及其二者的相互合和乃至于“生生”。由此可见,于“道”而言,“有”与“无”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相生相胜、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老子之“道”。
在对宇宙的演化过程予以描述之后,老子又对“万物”的特征予以论述,即其所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即意味着宇宙万物皆继承有“道”的“阴”和“阳”两种“基因”或特性。所谓“冲气以为和”之“冲”,古今学者大多解释为“虚”,认为由“虚气”化合“阴阳”二气。当然,此解无大碍于理解老子本意。实则,“冲”既可训为“虚”,又可训为“中”。《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云:“冲者,中也,是谓太和。”以“冲气”为“中气”解,则意味着“阴阳二气”相交,必生“中气”或曰“中和”“太和”之气。以“中气”为解,也恰与《中庸》所谓的“中”相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此解亦与老子所谓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更为切合。
至此,老子以寥寥数句即构建出其博大精深的宇宙观和本体论。老子之“道”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不仅暗合于“六经之首”的《周易》,更为令人惊诧不已的是,老子之“道”关于宇宙的衍生学说及其规律,与现代物理学中关于宇宙形成的“奇点”概念亦有诸多相似之处。所谓“奇点”,是指现代物理学上“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点”,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一种存在形式。“奇点”可谓“至小无内,至大无外”,它拥有无限大的物质密度和无限弯曲的时空。于“奇点”而言,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时空是一体的;“奇点”同时具备无限收缩和无限膨胀乃至于大爆炸进而生成宇宙的可能性。
人们通常认为,大凡哲学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与人生意义及道德修养并无大涉。实则大谬也。聆听老子之“道”的微言大义,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穷知宇宙奥妙的好奇心,亦足以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者”而设“教”,以及为“勤而行之”的“上士”之为“学”。由老子之“道”的宇宙演化过程可知,“一”或曰“太极”乃“道”之“本体”,人间万物皆源自于“一”或曰“太极”。抑或说,“一”或曰“太极”之“基因”业已为人间万物所共享,人间万物也因此而具有“共性”。由“万物负阴而抱阳”可知,人间万物又各自具备“阴阳”二性或曰各有“一太极”,故而人间万物又各具“个性”。可以说,正是借由人间万物“共性”与“个性”的相互消长与统一,才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
上文仅对老子之“道”的“生生”功能及其内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老子之“道”的“生生”,可归于老子哲学的宇宙观和本体论范畴。实际上,老子之“道”的内涵博大精深,还包括尊道、悟道、修道、返道等与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相关的诸多内容。由于古今中外学界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下文仅就老子之“德”的内涵及其与“道”的关系等予以简单分析。
严格而言,老子之“德”并非一个独立的“存在”,亦非一个本自具足的“概念”。从宇宙发生学来看,如果说“道”是世间万物的“生母”,那么“德”就是抚育世间万物的“养母”;就世间万物的运行而言,如果说“道”是世间规律的“制定者”,那么“德”就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就万物的本性而言,如果说“道”是万物不同“基因”的“赋予者”,那么“德”就是辅助万物“基因”之潜能发展的“成就者”;就世间万物循环往返的发展规律而言,如果说“道”是万物最终“返璞”的“归宿者”,那么“德”就是促成万物“归真”的“投宿者”。由此而言,“德”似乎是“道”的钦差“使者”,其所有的“使命”就是真实地向人间万物传递“道”的信息,进而辅助万物乃至于人间成全其自身。
老子之“道”之“德”与“万物”的这种关系,与基督教关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学说有一定的可比较之处。基督教所谓的“三位一体”,意指上帝是由“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共同构成的。“圣父”是世界万有的造物主,“圣子”即耶稣是“圣父”的独生子,也是被“圣父”派往人间的唯一使者和救赎者;而“圣灵”则是造物主的意志,通常经由“圣子”耶稣的言行传递给被造物。就二者的相似之处而言,“道”与“圣父”都是人间万物的本源,“德”与“圣子”耶稣都可谓上传下达的使者,而“圣灵”则可比拟为“道”经由“德”化育“万物”的“势能”或“信息”。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三位一体”的“圣父”上帝,是以“博爱”的形式来“救赎”业已“堕落”的人类;而老子的“道”与“德”则是以“无为”和“自然”的原则,来生育和畜养“一视同仁”的万物和人类。就同样作为“使者”身份的“德”和“圣子”耶稣而言,二者显露给人间万物的形象是迥然有别的。作为“圣父”独生子的“圣子”耶稣,一旦“道成肉身”由“天界”下凡到“人间”,其普遍神秘的“形上道性”也就必定会局限于特定时空中的“形下器用”。抑或说,尽管“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人间也具备“三位一体”的“位格”权威性,但是作为外显为“肉身”具体形象的“人”,他只能在“某时某地”对“部分人”传道进而对其“救赎”。与此相反,老子之“德”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形象的“存在”,在沟通“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时,可谓游刃有余,圆融无碍。老子之“德”对“形上”和“形下”贯通的特性,大凡盖因“形上”之“道”在生育“形下”的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类的同时,亦将自身“自然无为”的特性赋予于天地万物和人间。而作为最先“得道”且集“道”之大成的“德”,在承接“畜养”万物的天职时,只需顺应和辅佐万物故有的发展潜能及特性以成就其自身即可。
可以说,“道”与“德”之间这种“生”与“育”的分工,又相济互补而共成一统的体用关系,乃是老子学说的一大创举。举凡古今中外诸多哲学体系,在体与用、道与器、学与术、形上与形下的关系构建上,大都存在些许顾此失彼、重此轻彼甚或二元割裂等缺憾,能够如老子的“道”与“德”这样圆融二者且臻于一统者,当属寥若晨星。
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既然老子之“道”是万物之母、规律之宗、价值之源、返璞之归,几乎涵盖人间万物生长衰亡的所有环节,为何还要设计和构建一个并非独立存在的“德”,来承继、辅佐并完成“畜养”人间万物的任务?难道“道”在“生成”人间万物之后,不能继而对其“养育”并最终完成所有的环节吗?难道“道”不是全知全能的吗?
究其原因,或许有如下诸点。其一,天地万物并非由老子之“道”直接所生,而是经过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之间,品物流形,各有其母。由“形上之道”直接“畜养”万物,既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逻辑,亦不符合老子“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和“万物将自化”等一贯的主张。其二,尽管人间万物皆从“道”那里继承有“自然”的“共性”,但是不同事物又各有其本身发展的“自性”,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特定的条件。正如老子所谓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事物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道”“德”“物”“势”等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三,如果老子之“道”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毕其功于一役”地创造并完成世间万物和人类,那么“道”就势必会像“上帝”那样,成为万物尤其是人类顶礼膜拜甚或迷信盲从的无上权威,而这恰恰是为崇尚万物“自然平等”的老子所反对的。其四,或许也是最直接的动因,作为“通古今之变”史官的老子深知,在夏商周三代由“天子”沟通天与人而形成的礼乐制度,之所以最后以“礼坏乐崩”而告终,大凡因这种由“以人占天”构建而成的制度与文化,极易于酿成以“天道”之名而行“私欲”之实的痼疾。
或许,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老子构建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逐层向上效法的“四法”模式,以及“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四大”次序。在“四法”和“四大”中,“人”以及作为人间君主的“王”均被列在末位,其上尚有“地”“天”和“道”需要效法和尊重。这种对世间万物的秩序设计,打破了之前“天→天子→天下”之中“君权天授”的“权力”模式,首次将“人”和作为人间君主的“王”,皆置于“地”“天”和“道”之下。在之前的“权力”模式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人间万物必须按照既定的等级“名分”结构而安分守己;而在老子的“效法”模式里,无论是“人”抑或是“王”,都平等地处于“地”“天”和“道”之下或之中,都需要效法“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无私无偏之爱,最终合于“自然无为”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法”和“四大”中,老子并没有赋予“德”以任何位置。对于人类而言,在可见可知的“天地”与“玄之又玄”的“道”之间,似乎还存在着难以跨越的“天堑”。进而言之,只有在“形下”的“天地”和“形上”的“道”之间架起一座“天梯”,方能使“天堑变通途”。老子所架设的“天梯”,即是“德”。
《老子》“德经”首章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老子看来,人类一旦失却“自然无为”的“天德”或曰“天性”,就会导致由“道”到“礼”的逐步下落,即“道→德→仁→义→礼”。老子提出这样一个由“道”到“礼”的逐步下落过程,似乎也在暗示人类也可以通过修德进道,反向地由“礼”逐步升华至“道”的境界,即“得礼而后义,得义而后仁,得仁而后德,得德而后道”;亦即,“礼→义→仁→德→道”。在“道德仁义礼”五者中,老子将“道”与“德”划为“上德”的范畴,而将“仁义礼”划为“下德”的范畴。“上德”与“下德”之间区分的标准,乃是“自然无为”如否。抑或说,“道”与“德”之所以属于“上德”,盖因其符合“自然无为”的标准;而“仁义礼”之所以被划为“下德”,概因三者依次愈加不符合“自然无为”的标准。老子认为,属于“上德”的“道”与“德”是理想的人生境界,而属于“下德”的“仁义礼”则是需要改进和升华的境地。如此一来,似乎就出现了“上德”的理想世界与“下德”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二元区分甚或断裂,二者之间需要有某种媒介予以沟通。这个媒介,即是“德”。
如上文所及,老子之“德”并非是一个本自具足的独立的概念,它的内涵及属性通常根据其“得”自于“道”的状况而定。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德”,老学界通常所谓的“道一而德万”,即属于此。简言之,老子之“德”,存在于所有的人间万物之中。诸如,老子认为,“水”之所以被誉为“几于道”的“上善”,盖因其“利万物而不争”;“赤子”之所以天真近道,盖因其“含德之厚”。在“道德仁义礼”五者中,如果说“道”属于世界本原的“形上本体”,“仁义礼”则属于人伦的“形下之用”,那么“德”即是沟通“形上”之“道体”与“形下”之“器用”之间的“媒介”。“德”实际上兼具“形上”和“形下”两种属性。老子之“德”这种贯通道器、即道即器、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属性,使得其在“形上”与“形下”、“理想”与“现实”之间游刃有余,圆通无碍。
尽管从世界的本原而言,老子之“道”属于“形上本体”,但是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中,“道”也逐次将自身“自然”的特性传递给了人间万物;而作为最先“得道”的“德”,在承接和行使“畜养”万物的天职时,只需顺应万物故有的“自然”之“共性”,再根据不同物类和人间不同的“个性”,以“无为”的方式辅佐其成就自身即可。大凡盖因于此,作为世界本原的“形上”之“道”,经由“德”的上下沟通及对万物的畜养,而与“形下”的人间万物构成了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圆通无碍的循环系统,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周行而不殆”的盎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