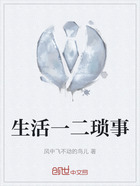
第3章 月 14日
梧桐树的影子斜斜切过挡风玻璃时,陈默闻到了槐花蒸腾的甜香。手机导航显示已到达明光小区西门,他摇下车窗,看见一位穿月白衬衫的妇人正弯腰和保安说话,手里提着鼓鼓的帆布袋。
“是方老师吗?“陈默探出头。后视镜里映出副驾驶座上的奥特曼玩偶,那是昨天儿子小树落下的。
妇人直起身,眼角的皱纹堆成温柔的弧度:“麻烦师傅开下后备箱,我这还有位'小客人'。“帆布袋忽然动了动,钻出个毛茸茸的橘猫脑袋,项圈上挂着褪色的铃铛。
陈默愣神的功夫,后备箱已经塞进三个扎着麻绳的纸箱。油墨味混着樟脑丸的气息在车厢弥漫,最上面那箱露出半截泛黄的奖状,写着“1998年度优秀教师“。
“去第七中学。“方老师抱着猫坐进后排,铃铛声清脆如教室檐角的风铃。小橘猫突然跃上中控台,肉垫按在导航屏幕上,陈默这才发现猫爪缺了一趾。
“当年地震时救学生伤的。“方老师轻抚猫背,指甲盖残留着蓝色墨渍,“它叫钢笔,跟我十五年啦。“
雨刷器划开渐密的雨幕,陈默瞥见后视镜里的女人正在摩挲一支脱漆的英雄牌钢笔。梧桐树影掠过她霜白的鬓角,那些被岁月磨亮的金属纹路,忽然让他想起父亲抽屉里同样款式的钢笔。
“现在的孩子像活在玻璃罩里。“方老师突然开口,钢笔在记事本上沙沙游走,“上周家访,孩子写错字就用修正带,雪白的纸面贴满补丁。“她摇摇头,笔尖在“自然“二字下重重画了道横线。
红灯亮起时,陈默看见第七中学的银杏树在雨中摇晃。二十年前他在这罚抄课文,墨水瓶打翻染蓝了袖口。父亲举着同款钢笔要揍人,是班主任拦住说:“墨迹洗不掉才好,长记性。“
“到了。“陈默提醒。方老师却示意他继续往前开:“先去操场东门,孩子们在等。“
雨帘中忽然冒出七八个撑伞的身影,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家长。穿红裙的女人小跑过来,发梢滴着水:“方老师,我家婷婷非要参加您的书法班...“话没说完就被戴眼镜的男人打断:“您说的无电子产品日,真能治孩子的拖延症?“
钢笔突然“喵“了一声。方老师打开帆布袋,掏出一摞毛边宣纸:“这是我用废试卷糊的练习纸。“陈默看见最上面那张还印着2003年的中考数学题,泛黄的几何图形上覆着崭新的墨字。
家长们传阅着宣纸低声议论,穿校服的女孩从人群钻出来:“方奶奶,上次您教我用毛笔修自行车链条,这次能学用墨汁补渔网吗?“她晃着断了背带的书包,金属扣在雨里闪着微光。
等最后一位家长离开,陈默忍不住问:“您退休十年了,怎么还...“后视镜里,方老师正用钢笔给猫梳毛,笔夹上的划痕在阴雨天格外清晰:“2008年5月12日,我在三楼给毕业班上最后一节书法课。“
雨声忽然变大。钢笔的铃铛发出细碎的颤音,像某个遥远下午的地动山摇。
“当时我们在练《兰亭序》,墨砚突然跳起来砸在讲台上。“方老师的声音很轻,“我举起钢笔指挥学生撤离,最后离开教室时,看见王小川还在捡他的修正带。“
陈默握方向盘的手猛然收紧。那个总坐在后排睡觉的男生,地震后再也没来上学。有人说他转学了,有人说他父母...
“钢笔就是那天捡的。“方老师挠着猫下巴,“它当时卡在废墟里,右爪被水泥板压着。我把它拽出来时,墨囊里的红墨水溅了一身。“
导航提示到达第七中学正门。陈默看见传达室墙上贴着“危房改造公示“,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往卡车上搬课桌椅。忽然有砂砾打在车窗上,他错觉听见了玻璃碎裂的脆响。
“要拆了。“方老师把脸贴在车窗,“那年地震后加固的裂缝还在墙上呢。“她指间转着那支旧钢笔,金属笔帽映出操场上飘摇的横幅,上面写着“共建现代化智慧校园“。
后备箱的纸箱在颠簸中发出轻响。陈默瞥见最上面那箱露出半截毛笔,笔杆上缠着胶布,墨色深深沁入木纹。他突然想起什么:“您刚才说钢笔是在地震时...“
“我丈夫的遗物。“方老师摘下眼镜擦拭,“他叫李文军,也是老师。03年非典时带着学生给隔离区送物资,感染走了。“钢笔忽然跳到她膝头,缺趾的爪子按住那个褪色的“军“字印章。
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扇形的水痕。陈默想起父亲总说“笔墨养人“,却在他高考志愿表上摔断了那支珍藏的钢笔。此刻后座飘来的桐油墨香,竟和记忆中父亲书桌的气息重叠。
转弯时,一个纸箱滑开,露出捆扎整齐的作业本。陈默看见最上面那本封皮写着“2008届毕业留念“,泛黄的纸张间夹着干枯的银杏叶,叶脉上还留着蓝墨水写的“好好活着“。
“到了。“方老师抱起猫,“这些旧物要捐给社区学堂。“她下车时,钢笔突然跳上引擎盖,缺趾的爪子按着雨痕,在玻璃上画出一道蜿蜒的曲线,像极了老校舍墙上的裂缝。
陈默打开手机,取消了下个订单。雨幕中的梧桐树下,他看见方老师正在给孩子们演示如何用毛笔给风筝线打结。断趾的橘猫蹲在砚台边,尾巴扫过宣纸上的新墨,那是个苍劲的“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