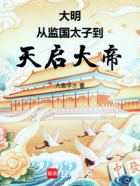
第27章 接班人袁应泰
一个人爱不爱读书,外人只能看到表象和态度,但不知道内心的想法。
就算是一名学渣,只要表现得努力又勤奋,家长或老师都会认可态度,但是成绩做不了假。
朱由校现在情况是,对外表现为好学的少年,且理解力、认知力都不错,完全是一个可造之材。
但其实,他并不好学。
翻来覆去的诵读经典,通过日讲官辅助了解含义,但最终要自己形成理解,从而发掘出治国的思路,这便是所谓的悟性。
古往今来的圣贤,能阅读到的文字相当有限,远不如未来学生阅读量,但这些先贤却能通过少量的经典,结合现实思考形成理论,然后以此施政与报国。
更有甚者,著书立说,惠泽后人。
诸如:阳明格竹,龙场悟道...
而朱由校不同,他不需要深入思考,由于多了几百年历史经验,很多明代无解的矛盾,后世有解决办法,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世界观、人生观、固有思维已形成,再想刻意改变可能性不大。
所以说。
每天满满的课程,只有书法是朱由校的唯一收获,其余知识进了脑海自动过滤。
而他表现得好学听讲,只不过要给那些超越时代的知识,一个合理的诞生渠道。
朱由校打算坚持一年,然后就以天才之姿正当辍学,把读书空出来的自由时间,全部拿来布局拯救大明。
在朱常洛病愈之前,朱由校还得帮着应付朝臣,他只对关键事件插手干预,普通政务则不去理会。
太子就干太子的活,没必要自己给自己上强度,遇到困难就推给老登处理,自己只是体验熟悉朝政,等朱常洛驾崩再大展拳脚不迟。
带着这样的心态,朱由校假后复课第一天,仍然听得专心致志。
很快就到了下午,体验治国的申时。
这一次,方从哲有事没来。
阁臣刘一燝、韩爌齐至,连同吏部尚书周嘉谟、兵部尚书黄嘉善,以及一个朱由校不认识的中年人。
相互讲理落座,朱由校看着陌生人不说话,黄嘉善当即介绍道:“殿下,此乃我部侍郎袁应泰,因他与今日议题有关,故带来文华殿相见。”
“袁应泰?”
“臣袁应泰,拜见太子殿下...”
袁应泰再行大礼,朱由校当即抬手示意,“刚刚已经见礼,袁侍郎快快平身。”
“多谢殿下。”
“快坐。”
朱由校殷勤劝坐,让袁应泰心生感慨。
他以前对太子没印象,但这几日在黄嘉善口中,得知朱由校好学勤奋,就是年幼没施政经验,且性格有点钻牛角尖。
今日见到真人,袁应泰就凭被太子礼遇这事,竟隐隐看到明君风范。
朱由校以礼相待,是因为知道袁应泰的为人,别看他官职不如黄嘉善,给朱由校的印象却深得多。
其由无他,盖因辽事。
历史记载的袁应泰,便是熊廷弼被罢免之后,临时代职辽东经略的人。
他以政绩做到兵部侍郎,说明其并非无能庸才,只不过没有带兵经验,也对战局没有正确认识,代职后便一改战略防御,带着平辽幻想转为战略进攻,最终连续丢了重镇沈阳、辽阳,致使辽河以东陆续沦陷。
按说袁应泰是丢城失地罪人,朱由校不应对他这么礼遇,但将战争失败全归他不客观,他有错误指挥的原因,也有麾下官员拱火之过,还有将士怯战退缩之由,更有后金用计且兵盛...
朱由校此时所敬,乃是袁应泰战败后的气节,他一个文人肯自缢谢罪,远远强过那些怯战武将,以及卖国通敌的投机者。
不得不说,此时的东林党人,很多慷慨悲歌之士,到了崇祯时期众正盈朝,蛇虫鼠蚁比比皆是。
对于魏忠贤,朱由校有心重新‘打扮’,对于东林党人,他也打算既用且防。
此时此刻,来到文华殿议事的五人,除了兵部尚书黄嘉善,其余四人都是东林党人,虽然不是众正盈朝,也间接说明东林党因有恩朱常洛,成为朝堂的优势一方。
而今日袁应泰出现,说明他们为熊廷弼挑的继任者,就是这位不知兵的兵部侍郎。
这就是东林党被诟病的原因,尽管有那么多忠义正直之士,他们也指出了各种社会积弊,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对策。
待到袁应泰坐定,朱由校明知道众人心思,开场却故意岔开话题。
“咦,本宫还以为方阁老要来,没想到换成刘、韩两位阁老,今日都有哪些政务?可千万不要太难啊...”
“殿下忘了?”
次辅刘一燝马上拉回主题,正色提醒道:“今日得敲定辽事,可不能再拖了。”
“对对对,本宫昨日微服出宫考察民情,竟然忘了这件大事,怎么样?有合适人选了么?
此话一出,除了刚接触他的袁应泰,其余四人心里都是同样念头。
太子这个年龄,说什么考察民情?只要陛下不开口惩治,贪玩又没人约束你。
不过吐槽归吐槽,正事还得继续办。
黄嘉善作为非东林党人,今日不但是其余人的点缀,还是袁应泰的隆重推荐人。
“前日听了殿下教诲,臣下来仔细总结与思考,发现袁侍郎资历够、有魄力、有决心,定能替代熊廷弼破虏平辽,所以臣举荐袁侍郎接任,请殿下定夺。”
“袁侍郎精干能臣,吏部存档的考察记录,无论京察外察皆上等,乃经略辽东不二人选,臣附议。”
周嘉谟出言佐证之后,韩爌则提醒袁应泰:“袁侍郎,你是怎么想的?也与殿下讲一讲。”
“是,阁老。”
袁应泰回应的同时,起身面对朱由校,铿锵说道:“臣必不负殿下与陛下期望,誓与辽东相始终,不破奴酋不返朝!”
“坐下说话,袁侍郎底气很足啊。”
朱由校笑呵呵挥手示意,紧跟着便转头闻周嘉谟。
“周尚书,本宫不了解袁侍郎,既然你们都认为合适,他应该是知兵的吧?吏部可有相关的记录?”
“呵呵,身为兵部侍郎,怎么会不知兵呢?”
周嘉谟笑着没正面回答。
朱由校遂转头再问袁应泰:
“袁侍郎,你以前有带兵成绩么?就算没有黄尚书那种‘三边大捷’,有周尚书剿抚平叛经验也行。”
“呃...”
袁应泰诚实对曰:“臣没有这些经验,但臣有信心经略好辽东。”
“没有?”
朱由校佯装诧异,顾盼左右后正色说道:“辽东乃大明门户,一旦有失京师危险,现在那里局势复杂,要是没有带兵的经历,只怕是难以胜任,可不是有信心就行的。”
“这...”
“本宫前日说过,会用兵不可或缺,周永春就没同意...”
“殿下。”
刘一燝见朱由校不悦,当即接话语重心长劝曰:“袁侍郎虽没带兵经历,但其在兵部为官耳濡目染,且他既有破虏决心,何不让其一试?眼下群臣弹劾不止,熊廷弼又怯战请辞,辽事已不能再拖...”
“既如此,就令熊廷弼继续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