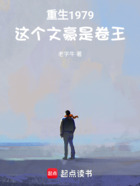
第94章 文学苦旅
后坨子大队,废弃知青点。
“别整啦!孩子死了来奶,有个屁用?!”
生产大队长踢一脚正在撅着腚修门的男人骂道。
男人白一眼大队长,不高兴地撇撇嘴,收起工具,敢怒不敢言地走了。
大队长恭敬地打开知青点那个快散架子的门:“领导,您请。”
县宣传部干部没有进屋,而是停下脚步朝着后面的记者伸出手:“记者同志,你们先请。”
记者们也没有进屋,同样停下脚步,朝着后面的十几人伸出手臂:“知青同志们,你们先请。”
苏文天朝着大家招招手:“咱们就别客气了,进屋吧。”
邹娟、林如心和当年“沙坨子知青文学社”的十几人人“呼啦啦”向屋里走去。
一名摄影记者突然冲出人群,两步跑到屋子中间,猛回头“咔嚓咔嚓”按下快门。
“坨子知青文学社”的知青们进到屋子里,看着这破败的样子,各种深刻和不深刻的感慨。
他们是真没想到,最后一位知青离开这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里就变得如此破败。
感慨了,一会儿之后邹娟拍拍手:“同学们,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怎么样?”
“对,收拾完咱们坐下聊。”林如心也随声附和。
“好好好。”
知青们纷纷抄起扫帚,笤帚,铁锹、抹布等,开始收拾屋子。
很快,知青点儿就被收拾干净。
苏文天对着生产大队长笑着说道:“赵叔,咱们现在上菜怎么样?”
“没问题。”
赵大队长说完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几个社员走进来,他们把这八张炕桌放在南北大炕上。
随即,一盆盆热气腾腾的手把羊肉全羊汤就端了上来。
大葱、大酱、茄子,辣椒,西红柿,熟米水饭,贴大饼子……
还有从四队水库里捞上来的草鱼,鲢鱼,泥鳅鱼……
最后,一个精壮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一个硕大的酒坛子走进来。
他“咚”的一声把酒坛子放在南炕上苏文天身后:“天儿,这是后屯子老郭头家的老烧,喝完还有呢。”
这小子正是赵二瘪,他打开酒坛子盖,浓浓的酒香瞬间飘满整个屋子。
“二瘪,一起吃吧。”苏文天发出邀请。
“这不中。”
赵二瘪摇摇头,转身走了。
知青们脱鞋上炕,将八张炕桌团团围住。
县里和公社的陪同干部们,也都围着桌子坐好。
满桌食物,满屋飘香,空气中充满着欢笑。
周娟端起酒杯:“同学们,在说正事之前,我想先敬苏文天一杯,大家同意吗?”
“同意!”
“必须同意!”
“嘎嘎同意!”
“贼拉同意!”
大家笑着、附和着、起哄着。
今天这个场面是苏文天一手安排的,大家能在别离之后这么久又重新聚在一起,还真得感谢苏文天。
这正是苏文天的第一步计划——“文学苦旅”。
他先是跟《东大青年报》的记者大卢说清楚,某省周报那个所谓的“沙坨子上放羊”是假的。
但他也没有答应大卢的专访,更没打算写一篇文章去揭露那个假的“沙坨子上放羊”。
如果他这样做,就陷入到“自证”的被动中。
而事实上,“沙坨子上放羊”所有的文章都是以手抄本方式在民间流行,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是公开发表过的。
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根本拿不出坚实的证据。
虽然他可以让当年“沙坨子知青文学社”的社员们给他作证,但对方要是也找来这样一帮人怎么办?
很有可能会陷入“真假孙猴子”的长期论战中。
当人们再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时候,最终就只能不再信任那个“沙坨子上放羊”的笔名。
所以苏文天采取的策略不是急于自证,而是迎风而起!
既然大家都说沙坨子上放羊重出江湖,那他就把动静闹的大一点、再大一点,给人一种大鹏扶摇九万里的感觉。
所谓“文学苦旅”,就是把原来那些“沙坨子知青文学社”的文学青年们再续前缘、重游故地。
邹娟虽然已经“不当社长好多年”,但号召一经发出,立刻就有响应。
这些昔日的文学青年,现如今大多都已“梦碎”,工作在各种自己不曾想过的领域,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最终,有10人表示坚决参加活动。
苏文天也大方地表示,无论从哪个城市而来,所有食宿路费全都报销,而且每人每天补助5元。
一天5元钱,这哪里是旧友相聚,分明是捞外快吗。
听到这一消息,立马又有十多个人要参加,但邹娟表示本期名额已满,等待下次吧。
对《东大青年报》苏文天则表示,这次“文学苦旅”活动,他将首次通过《东大青年报》向文学界透露自己的身份。
《东大青年报》可以独家报道他们这次活动。
但他更希望,《东大青年报》在发表大篇幅通讯报道的同时,也可以适当给其它媒体和文学刊物透露一点点消息。
这样无论是对“文学苦旅”这个活动,还是苏文天都会产生更广的传播效果。
而且那些人要想知道更详细信息,肯定会寻找《东大青年报》,这样对《东大青年报》也是一种推广。
《东大青年报》文学编辑室主任听了苏文天这些设想之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当苏文天接着把第二步和第三步计划也说出来后,文学编辑室主任立刻坐不住,当即离席把苏文天的计划向总编辑做了汇报。
总编辑听了汇报甚是惊讶,他亲自出马面跟苏文天敲定了计划的方方面面。
就这样,一个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宏大的媒体活动计划应运而生……
“咱们这次活动,所有费用都是文天所出。”邹娟不遗余力地介绍着,“就今天这顿饭,文天出了足足有200元钱给生产队。”
“哇!”
“天呐!”
在座的很多人都发出了惊呼。
这些知青,都回城没几年,一个月工资再高也不会超过50元,一般只有三十十元的样子。
苏文天一下子拿出200元钱,怎么能不让他们惊讶。
更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苏文天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他现在是做什么的?怎么如此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