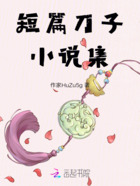
第2章 未接来电
第一节
林清月的生物钟精准得像座老钟。每天下午三点,她必端着搪瓷杯坐到客厅藤椅上,杯里泡着老伴周建国最爱的碧螺春,茶叶在玻璃杯中浮沉,像极了他讲课时常比划的手势。今天是秋分,窗外的梧桐落了第一片叶子,金黄的叶尖擦过玻璃,在窗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恰好落在茶几边缘的座机上。
那是部银灰色的固定电话,机身刻着细密的缠枝花纹,听筒线被磨得发亮,露出底下黑色的橡胶。周建国退休那天把它抱回家,像捧着什么宝贝:“清月你看,这机子声音清楚,以后在家等学生电话,得用个像样的。“彼时他刚从市一中退休,教了四十年语文,办公室的电话成了他另一个器官,退休后总念叨着“怕学生找不着人“,于是斥巨资买了这部当时最时兴的按键座机。
此刻座机屏幕暗着,只有边角的时间显示:15:17。
林清月的指尖在藤椅扶手上轻轻敲击,节奏和挂钟的“滴答“声重合。她望着座机,眼神有些涣散,仿佛透过冰冷的机身,能看见某个熟悉的身影。三年了,自从周建国走后,这把藤椅、这杯茶、这部电话,成了她对抗时间的全部阵地。
“老头子,今天茶泡浓了。“她忽然开口,声音在空荡的客厅里显得有些发飘,“你总说我不懂茶,得用80度的水,不然伤了茶气。“
无人回应。只有风穿过纱窗的缝隙,发出细微的“嘶啦“声。
她想起周建国去世前的那个下午。也是九月,天气微凉,他靠在沙发上,脸色比往常更白些,额头上敷着毛巾。“我去给你端药。“林清月起身时,他抓住她的手,指尖有些发烫:“不急,先陪我坐会儿。“
可她还是去了厨房。瓷勺碰着药碗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等她端着药出来,就看见周建国盯着座机屏幕发呆,眉头皱得紧紧的。“怎么了?“她问。
他抬起头,勉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没什么,一个未接来电,号码挺陌生的。“他把电话递给她,屏幕上赫然显示着:2022年9月15日 14:37,未接来电。归属地是邻市。
“说不定是哪个调皮学生搞恶作剧。“他说着,把电话放回茶几,声音带着病中的沙哑,“快把药给我吧,苦死了。“
那时她没多想,只当是骚扰电话。直到三天后,周建国在凌晨突发心梗,被救护车拉走前,还抓着她的手念叨:“清月,我好像……有什么事没做完……“
什么事呢?她想了三年。
第二节:皱巴巴的纸条
葬礼在一个雨天举行。黑色的伞挤满了灵堂,周建国的学生们从各地赶来,有头发花白的教授,也有刚毕业的年轻人。林清月坐在角落,看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忽然觉得丈夫的一生像棵大树,枝枝蔓蔓延伸到四面八方,而她只是守着树根的人。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走到她面前,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条,指尖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师母。“他声音哽咽,“我是周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叫陈凯。“
林清月点点头,印象里周建国确实总提起这个学生,说他“笨鸟先飞“,当年为了考大学,在办公室待到半夜背书。
“这是周老师三年前留给我的号码。“陈凯把纸条展开,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串数字,字迹是周建国特有的遒劲,“他说等我考研成功了,就打这个电话报喜,他要请我吃他做的红烧肉。“
林清月的心脏猛地一缩。那串数字,赫然是三年前那个未接来电的号码。
“我……我考上了邻市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陈凯的眼镜片上蒙着水汽,不知是泪还是雾,“复试通过那天是9月15号,我太激动了,第一个就想告诉周老师……电话通了,响了几声就被挂了,我以为是信号不好,再打就没人接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后来我忙着办手续,想着开学了去看他,没想到……“
林清月接过纸条,纸张边缘被磨得毛糙,显然被人反复看过。她想起周建国去世前那几天,总是时不时拿起座机看看,有时对着屏幕发呆,有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摇摇头。她以为是病痛让他糊涂了,却不知道他是在等一个电话,一个来自二十年前学生的,迟到了太久的报喜。
“他总说,你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学生。“林清月的声音也抖了起来,“说你当年考大学不容易,家里条件差,总吃不上热饭……“
陈凯猛地抬头,眼里全是震惊:“周老师……他怎么知道?我从没跟人说过……“
“他啊,“林清月看着窗外的雨,想起周建国深夜批改作业时,总会喃喃自语某个学生的名字,“他什么都知道。你大三那年冬天,没钱买羽绒服,是不是收到过一个匿名的包裹?里面是件蓝色的棉袄?“
陈凯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用力点点头。
“那是他偷偷托我寄的。“林清月的视线模糊了,“他说你这孩子犟,不肯接受接济,只能用这种办法。“
雨还在下,敲打着窗玻璃,也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陈凯手里的纸条被泪水浸湿,周建国的字迹在水痕中晕开,像一幅逐渐模糊的画。而林清月心里那个长久以来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周建国临终前说的“没做完的事“,原来是在等这个电话,等他最牵挂的学生,亲口说一声“我做到了“。
第三节:日记本里的字迹
整理周建国遗物时,林清月在书柜最底层找到了一个上锁的木盒。盒子是他年轻时自己做的,边角刻着笨拙的花纹。她用他常用的那把铜钥匙打开,里面除了几张老照片,还有一本厚厚的日记本。
日记本的纸张已经泛黄,第一页写着“周建国的教学手记“,日期从1982年开始,一直记到2022年9月12日,也就是他去世前四天。
林清月戴上老花镜,指尖颤抖着翻开。里面大多是教学心得和学生记录,字迹工整,偶尔夹杂着几句对生活的感慨。她翻到2002年,看到了陈凯的名字:
“9月5日,陈凯这孩子又在办公室待到天黑。给他泡了杯糖水,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支支吾吾说'家里没人'。这孩子自尊心太强,得找个合适的办法帮他。“
“12月20日,天气真冷。看见陈凯穿着单衣在走廊背书,鼻子都冻红了。晚上回家跟清月商量,把我那件旧棉袄找出来,明天偷偷放他柜子里。“
一页页翻过去,陈凯的名字像条细线,贯穿了周建国的十年教学生涯。直到2020年,日记本里再次出现关于他的记录:
“5月10日,碰到陈凯了,在学校门口的书店打工。这孩子还在考研,考了两次都没考上,看着让人心疼。跟他说别灰心,老师等他好消息。他笑着说:'周老师,等我考上了,第一个给您打电话报喜,您得请我吃红烧肉。'我说:'好,我在家等着。'“
林清月的眼泪滴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墨迹。她想起那之后,周建国真的开始研究红烧肉的做法,买了本菜谱放在厨房,没事就戴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嘴里还念叨着:“陈凯这孩子,爱吃甜口的,得多放点糖。“
她翻到2022年9月12日的记录,那是周建国去世前最后一篇日记:
“今天心口还是不舒服,清月让我去医院,我没去。总觉得心里有事放不下。陈凯这孩子,今年该第三次考研了吧?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等他电话呢,得把座机充好电,可不能漏了。清月说我瞎操心,她不懂,那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儿子……“
后面的字迹有些潦草,似乎写着写着就没了力气。林清月合上日记本,把脸埋在手里,压抑了三年的哭声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原来他不是糊涂,不是唠叨,他是真的在等,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守着一个二十年前的约定,等着那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打来一个报喜的电话。
而她,却在那个关键的下午,因为一杯药,错过了。
第四节:听筒里的忙音
秋分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林清月依旧每天下午三点坐在藤椅上,只是现在她不再只是发呆,而是会拿起座机,一遍遍地看着那个未接来电的记录。号码她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像刻在骨头里一样。
陈凯来看过她几次,每次都带着水果,坐在沙发上陪她说话。他现在是邻市一所中学的老师,说起话来有了周建国当年的影子。“师母,您别太难过了。“他总是这样说,“周老师知道我考上了,他肯定替我高兴。“
林清月点点头,却还是忍不住问:“小陈啊,你那天打电话的时候,真的……听到接通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师母。“陈凯很肯定,“响了大概三四声,然后就被挂断了,再打就提示正在通话中,后来就没人接了。“
三四声。林清月在心里默念着。她去厨房端药,再回到客厅,大概就是三四声的时间。如果当时她走快一点,如果当时周建国能撑着多等几秒,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这个念头像根针,每天都在她心里扎一下,不致命,却足够疼。
这天下午,她看着座机屏幕上的时间跳到15:17,和三年前那个时刻一模一样。窗外的梧桐又落了几片叶子,在窗台上堆成小小的一堆。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颤抖着拿起听筒。
“嘟——“
听筒里传来清晰的拨号音。她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数字,每按一下,心脏就跟着跳一下。
“嘟——嘟——“
电话通了。
林清月屏住呼吸,耳朵紧紧贴在听筒上,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格外清楚。她想象着电话那头可能出现的声音,是陈凯惊喜的“师母“,还是某个陌生人的“喂“?
“嘟——嘟——“
响了四声,和陈凯说的一样。
然后,听筒里传来了那个她既熟悉又害怕的声音: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Sorry,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机械的女声,冰冷,没有任何感情,像一把钝刀,缓缓割过她的心脏。
空号。
原来这个号码,在周建国去世后不久就被注销了。也许是陈凯换了号码,也许是运营商回收了号码,总之,再也打不通了。
林清月握着听筒,久久没有放下。听筒线从她指间滑落,垂在茶几上,像一条断了的脐带。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斑白的头发上,也落在座机屏幕上——未接来电的时间依旧显示着14:37,像一个永恒的伤口,凝固在三年前的那个下午。
她忽然想起周建国去世前那晚,拉着她的手说“有什么事没做完“时,眼里的焦急和茫然。现在她明白了,他不是没做完事,他是没等到。等一个电话,等一句报喜,等一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孩子,告诉他“我没让你失望“。
而她,是那个唯一离他最近,却没能帮他等到的人。
第五节:藤椅上的阳光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像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生了又落。林清月依旧每天下午三点坐在藤椅上,只是不再盯着座机发呆。她把座机擦得干干净净,放在茶几最显眼的位置,偶尔会对着它说说话,像和周建国聊天一样。
“老头子,今天小陈来看我了,说他带的班考了年级第一,跟你当年一样厉害。“
“老头子,楼下张阿姨送了我些新茶,你尝尝看,是不是比上次的好。“
“老头子,秋天了,你那件厚毛衣我找出来了,放在衣柜里,明年春天再收起来。“
她不再去想那个未接来电,不再去想如果当初。有些遗憾,就像落在窗台上的梧桐叶,扫掉了还会再来,不如就让它留在那里,成为日子的一部分。
这天下午,阳光格外好,透过纱窗洒在客厅里,暖洋洋的。林清月坐在藤椅上打了个盹,迷迷糊糊中好像看见周建国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教案,笑着说:“清月,我回来了。“
她猛地睁开眼,客厅里空无一人,只有座机在阳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
她笑了笑,摇摇头,觉得自己是老糊涂了。
起身准备去厨房做饭,路过茶几的时候,无意间瞥了一眼座机屏幕。
屏幕没有暗下去,而是亮着,显示着一个新的未接来电记录:
2025年10月23日 15:17,通话时长:00:00
号码很陌生,归属地是邻市。
林清月的脚步顿住了。她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号码,心脏又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是巧合吗?还是……
她伸出手,指尖悬在听筒上方,犹豫了很久。阳光落在她的手上,把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
最终,她还是没有拿起听筒。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秋日的风带着桂花的香气吹进来,暖洋洋的,像谁的手轻轻拂过她的脸颊。楼下传来孩子们的笑声,还有自行车的铃铛声,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遥远。
她想起周建国常说的话:“教书啊,就像种树,种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可你只要耐心等,总能等到的。“
也许那个电话,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牵挂的孩子,终究是长成了大树,而他种下的那些爱与希望,也早已在时光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林清月关上窗户,转过身,对着茶几上的座机笑了笑。
“老头子,“她轻声说,“饭要凉了,回来吃饭吧。“
阳光穿过玻璃,落在藤椅上,落在座机上,也落在她的身上,把一切都染成了温暖的金色。那个未接来电的记录,静静地躺在屏幕上,像一个温柔的秘密,被时光妥善收藏。而有些声音,即使没有通过听筒传来,也早已在彼此的心里,说了千遍万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