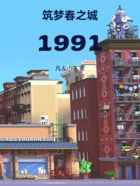
第15章 北极星计划
1991年10月的昆明,雨裹着寒风撞在蜂鸟小店的玻璃上,李天宇盯着报纸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的标题,指尖在“莫斯科”三个字上反复摩挲。
小敏突然拽了拽他的袖子,往柜台后努嘴——杨教授正蹲在那里,用放大镜研究那台老式打印机,镜片反射着窗外的阳光。
“杨教授的大儿子在苏俄搞船舶工程,”小敏压低声音,“您忘了他书架上那本《船舶工程》?每月都有儿子寄来的期刊,里面夹着黑海造船厂的图纸复印件。”
李天宇突然想起,杨教授在翠湖边翻给王磊看的破冰船照片,还有那句“航母甲板钢配方都标着,可咱们短时期造不出来”。
他深吸一口气,往柜台走时,脚步在杨教授身后顿了顿
——老人正用红铅笔在一张便签上写着什么,字迹和当初夹在捐赠书里的“科技传承,星火不息”如出一辙。
“杨老师,”李天宇蹲下来,指尖敲了敲打印机的齿轮?
“您说这苏俄的破冰船钢,要是能弄点样品回来,咱们的造船厂会不会少走十年弯路?”
杨教授笔尖一顿,红铅笔在纸上洇出个小团:“小孩子家别瞎想,国家大事轮不到咱们操心。”
但他攥着放大镜的手,指节却泛了白——李天宇瞥见便签上写着“致长子:速查仓库第3排第5箱,船舶钢样勿遗失”。
小敏突然把那张苏联局势的报纸推过去,指着角落的天气预报:
“您看,列宁格勒这周零下25度,黑海造船厂的工人们怕是连暖气都没了。”
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雪落,“我爸以前在档案馆抄过资料,说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帮咱们建工厂时,总把‘技术无国界’挂在嘴边。”
这话戳中了杨教授的软肋。他曾跟李天宇说过,自己当知青时,正是靠苏联专家留下的农机手册,才在云南山区种出了高产水稻。
老人突然起身,往三楼走时丢下句:“你们跟我来,有东西给你们看。”
三楼英语角的书架后,杨教授撬开块松动的地板,里面藏着个铁皮盒。打开时,一股樟脑味混着油墨香涌出来
——全是他大儿子从苏联寄来的信件,最上面一封盖着11月的邮戳:“爸,厂里发不出工资,有人开始偷偷卖仓库里的图纸,说能换面包。”
既然把信藏在别人的屋里头。
“这就是你们说的‘机遇’?”杨教授的声音发颤,指着信里的一句话。
“‘第12车间的发动机图纸,被保加利亚商人用三箱罐头换走了’——这哪是机遇?是剜心!”
李天宇突然想起,自己劝杨教授搞“理想国”游戏时,老人那句“三十年前的梦,看你们能不能圆”。
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纸,上面是小敏画的中文传呼机草图,旁边标注着“需苏联产144KHz芯片”:
“我们不是要偷,是想请您儿子帮忙‘保管’些东西。比如那些卖不出去的芯片手册、发动机参数,先寄到咱们的智库来,等将来苏联稳定了,再原封不动还回去。”
“你们想让他犯法?”
杨教授把铁皮盒摔在桌上,信件散落一地。其中一封飘到李天宇脚边,是《舰船知识》期刊内页,上面有长子用红笔圈出的句子:“中国朋友若需,可优先提供技术支持”。
小敏捡起那页纸,突然笑了:“杨老师,您还记得给我们的《少年科学画报》吗?里面有篇讲苏联宇航员的文章,说加加林上天前,特意带了各国科学家的签名照。”
她指着照片里的中国科学家,“那是您的老同学吧?照片背面写着‘为了人类共同的星空’。”
杨教授盯着照片,突然从怀里掏出个旧信封——正是李天宇见过的,夹在1956年《科学通报》里的那张,上面印着“中苏技术合作办公室”。
老人抖着手,从里面抽出张泛黄的通讯录:“我大儿子的同学,在图波列夫设计局当工程师,这是他家的电话。”
他顿了顿,红铅笔在传呼机草图上重重一划:“芯片手册可以要,但得跟人家说清楚,是为了‘交流’,不是‘倒卖’。
还有,让他多寄几本航空发动机的书——我那孙子将来想考北航,说要造咱们自己的大飞机。”
李天宇和小敏对视一眼,看见对方眼里的雪光都亮了。
杨教授突然又把铁皮盒锁上:“这事得跟智库的老伙计们商量,他们有不少老战友在东北边境,能帮忙把东西运过来。
但有一条,所有资料都得登记造册,将来国家要,咱们得能拿出来。”
下楼时,李建强正把刚焊好的传呼机样机摆在柜台上,屏幕上用LED灯拼出“蜂鸟”两个字。杨教授摸了摸样机,突然对李天宇说:
“你上次说的游戏,叫‘理想国’是吧?加个新关卡——‘冰雪里的信使’,让玩家护送技术资料穿越边境,通关奖励就叫‘星辰大海’。”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李天宇看着杨教授往邮局的方向走,老人怀里揣着给长子的电报,信封上写着“父字:以技术之名,护星火不灭”。
他突然想起王磊收书时,杨教授说的那句“看书不光是记知识,得琢磨怎么用”——原来有些书,从来就不该躺在书架上。
1991年12月15日,昆明理工大405宿舍的暖气片上晾着五双袜子,窗台上的煤油灯把六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挤挤挨挨的群像画。
李天宇把一张苏联地图铺在床板上,红铅笔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位置画了三个圈——这是他们从杨教授大儿子的信里圈出的“人才密集区”。
“黑海造船厂的船舶工程师,第聂伯河沿岸的微电子专家,还有拜科努尔航天中心的火箭设计师。”
李天宇用铅笔尖戳着地图,“这三个圈里,至少藏着两千个能帮咱们跳过十年技术弯路的人,至于高级技术工程师,那可能是上万人,现在一直到明年,后年他们里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科学技术,他们需要的是面包,食品,衣物。”
江大河啃着半截馒头,把“北极星行动计划”的草稿翻得哗哗响:
“我算过账,按人才引进每人二十万美元算,一万名就是二十亿。国家现在外汇储备刚过两百亿,肯定拿不出这笔钱。
但华润在香港有外汇额度,上次跟他们谈计算器代理时,王经理说能从南洋银行贷到低息款——前提是咱们得有抵押。”
“抵押?”
徐光裕从枕头下摸出个铁皮饼干盒,倒出里面的传呼机样机,“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
他是浙江人,算盘打得精,早把蜂鸟小店的资产盘了三遍,“咱们现在账上只有八千块,连去莫斯科的机票都买不起,所以靠我们几个阿猫阿狗这件事没有任何可能可以办成。”
王磊突然想起什么,拽着李天宇往三楼跑。
英语角的黑板上,袁蔚兰刚写完“中苏友谊”四个粉笔字,旁边粘着张泛黄的老照片
——1956年,杨教授和苏联专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合影。
“闫老师说,那批专家里有个叫安德烈的,后来成了第聂伯河微电子研究所的所长。”
王磊指着照片里戴眼镜的年轻人,“他女儿现在在云南大学读中文系,上周还来英语角练口语,你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
这消息像团火,把宿舍里的愁云烧得精光。
当晚,杨教授带着安德烈的女儿卡佳来到蜂鸟小店。
女孩裹着件旧军大衣,掏出本笔记本:“你们的事情有点大,不过我考虑过,也告诉了我的爸爸。
我爸爸昨天打电话说,研究所的暖气停了,他正把芯片设计图往地窖里藏,知道那些芯片设计图纸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
在我们那边要吃饱肚子过日子,不会再有那么多钱投入到那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设计上面了!”
笔记本里夹着张名单,上面是三十七个愿意“暂时借调到中国”的科学家名字,“他们不要美元,只要面粉、毛毯和能让孩子上学的名额。”
李建强蹲在角落修收音机,突然插了句:“我在工地上认识个河南老乡,现在跑中蒙边境贸易,能用羽绒服换蒙古的羊皮。
要不咱们往北边倒腾点过冬物资?”李秀兰跟着搭话:“我妹妹在昆明罐头厂当厂长助手,厂里的水果罐头堆成山,换面包肯定行。”
计算机所的助理研究员陈明远连夜把计划抄送给省科委。
第二天一早,云南大学谭副校长就带着理工大学陈副校长找上门,手里捏着封盖着红章的信:“省里头批了,说这是‘民间科技交流’。
闫文龙老师已经联系上当年参与156项计划的老同志们,他们联名写了封信给外交部,说要‘接老朋友回家’。”
严天羽却泼了盆冷水:“光有物资和信没用。哈萨克斯坦那边乱得很,上周有批波兰商人想接科学家,半道被民兵扣了。
咱们得找个能打通关节的——我在香港的表哥说,华润有支安保队,全是退役的解放军侦察兵。”
这话点醒了李天宇。
他翻开杨教授给的通讯录,找到个名字——“赵建国,华润驻莫斯科代表处,1968年毕业于哈军工”。
电话接通时,那边传来噼里啪啦的打字声:“我等你们这句话等了三个月。
西伯利亚航空有架货机明天飞BJ,机腹能藏二十个人——但你们得搞到苏联民航的调度密码。”
小敏突然想起父亲的档案馆里有份1989年的《中苏民用航空协定》,里面附着加密方式。
凌晨三点,王磊和徐光裕破译出密码时,窗外的梧桐树上落了层薄雪。
李天宇在行动计划的最后添了句:“1992年元旦,让第一批科学家坐上南下的火车,这是北极星计划的第一批,他不会停了下来。”
卡佳把父亲的芯片手册铺在柜台上,杨教授用红铅笔在扉页写下:“技术无国界,就像五十年代他们帮我们那样。”
“亲爱的卡佳同志,你告诉你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五年以后,你们国家如果好转了,或者说你们想回去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拦你们,仍然还带着你们研究出来东西,跟你们国家分享!
比起有些人去了美国之后,永远成为敌对国家的一员,要好得多,你们内心深处一定是热爱你们的国家的!”
李天宇摸着手册上安德烈的签名,突然明白北极星的真正含义——不是把星星摘回家,而是让星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
宿舍里的煤油灯燃到天明,地图上的三个红圈旁,被江大河用毛笔添了行字:“从云南到第聂伯河,用罐头换一个未来。”
历史上有人用衣服,罐头和方便面替川省换来了两架民航飞机,1991年后就是这么疯狂年代。
远处的广播里,正播放着苏联解体的新闻,但蜂鸟小店的人谁也没听
——他们忙着给北上的卡车装罐头,给科学家的孩子准备课本,仿佛已经看见,那些裹着军大衣的身影,正踩着雪朝中国的方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