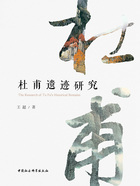
序二
孙尚勇
杜甫大约是孔子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生长出来的最伟大的知识者之一。他早年南适金陵吴越,东游梁宋齐鲁,经历了一段同时代多数文士和知识者共有的“裘马颇轻狂”的恣意生涯。中岁误落尘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以圣贤自期,意图实现“致君尧舜上”的崇高政治理想。胸怀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抱着理想政治的预期,然后矢志不渝地去追寻个人的政治理想,持此种先入的思维行事,势必遭受种种挫折。在遭受终极的挫折之后,理想主义者又更易于体察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政治社会的弊端。于是对人和文化无比的爱与犀利的政治社会批判情绪,似乎悖论般叠加于理想主义者一身。孔子如此,杜甫亦是如此。天宝三载,杜甫与宿心相亲的李白相遇,他从刚刚失意归山的李白那了解到朝中政治状况,却仍然在一年多后踏着李白失败的脚印,兴致勃勃西归咸阳谋求政治发展。杜甫吸取了李白的经验教训,收敛了他和李白共通的清狂,如其诗中所说,“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为了“功名”和“权势”,违心地“朝扣”“暮随”。十年京华,杜甫体验了后来屡屡反思且深以为愧耻的种种遭际。因缘于投匦献赋,他得以短暂逍遥于太子右卫率府。不幸安史之乱将大唐盛世的所有荣光一举击碎,华夏文明惨遭荼毒,这也几乎摧毁了杜甫实现宏大政治理想的最后希望。“国破山河在”,怀着对文化的期冀和热忱,杜甫从陷于贼手的长安城,间道奔赴凤翔,授左拾遗,成为成就肃宗中兴的众多小人物之一。然而,由于牵裾直言而获罪,长安收复之后,他由左拾遗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在最上层政治中心圈边缘活动的四五年间,杜甫愈加清晰地认识到理想政治之不可期。于是他毅然告归西向,辗转秦州、同谷,在成都一带定居数载,旋复沿江东下至云安、夔州,漂泊江陵湖湘,在一个谋欲“归秦”的炎冬客死孤舟之上,带着无所成就的怅恨,走完了艰难悲壮的一生。
一 杜甫的文化反思
三十五岁西归咸阳,四十四岁居官,四十八岁罢官,杜甫的活动中心是长安,是为杜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十四年。从四十八岁罢官到五十九岁往生,杜甫人生最后的十二年,跟孔子在外十四年一样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由最后十二年“吾道”“吾老”“吾衰”“今如丧家狗”“或似丧家狗”等与孔子相关联的表达来看,跟孔子周游列国相类,杜甫对现实政治始终保留着些许信念,默默等待“苟有用我者”,期盼中原书信。但现实何其不幸,又何其残酷,他没能等到终不改的北极朝廷的召唤,甚至没能像孔子那样回归鲁国,杜甫最终没有实现“不死必归秦”的心愿。“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从杜甫一生的行迹,似可窥见他心目中孔圣的影子。杜甫“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等诗句,其“壮心”常在的表达,由此方可获得理解。
前贤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然而汉武帝盛世蜀中文人司马相如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只能说是一个勉强的误解。假如历史可以重来,给他一个稍稍恒长的盛世,给他一个真讲理想的时代,杜甫照样能够做到立言,而且能够实现立功,乃至立德。如杜甫自己所说,“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无疑,杜甫终其一生为理想奔走,为国家和文化呼号,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哀伤寂寞的,但对于中国文化却是壮阔雄奇的。钱穆有言,杜甫是意欲求有所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但他却以多病之身承担了文化兴衰之大责任,他是在现实事功上无所表现却主宰历史的大人物之一。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奉杜甫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然而在诗之外,杜甫留给我们更为重要的遗产是他的精神和思想,是他从孔子那儿继承而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责任感。
人类世界有许多未知和不确定。尽管我们一度竭力去追求,甚至放弃自我的尊严,但仍然不能确保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实现,因为我们会有偶然的怠惰,会有必然的疏失,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个体总归受制于历史。当人生经历愈加丰富,人们会更多地渴望了解和确定。但人和世界和我注定了这渴望是一种徒劳。杜甫近六十年的人生,四十余年的履世,其间尚有许多我们所未知和不确定的问题。有一点可以确定,杜甫是盛唐文化培养出来最优秀的代表者,是盛唐文化一个焕发着独特异彩的人物。
王昌龄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这是感叹时无良将,不能安边。在所谓唐人边塞诗中,这是较为常见的情感表达。静言思之,类似诗篇可以视作对当时将领的严厉批评,这一批评似乎很容易便获得正面的肯定。将领不能安边,不能体恤士兵,将领在暖帐轻歌曼舞,士兵却严寒刁斗,肯定不合道义。但是,安边抚卒的龙城飞将,无非首要是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对周边族群形成军事威慑,故归根结底,这些诗篇所推扬的是军事和战争。从人类文明的立场看,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人群之间必然要以和平共存为相处模式,鼓吹发展和使用武力,就其终极来说,无疑是不合于人道的。尤其当一个强大的国家,已经在文化和文明上对周边族群形成了优势,这时候继续鼓吹武力显然是不道德的。盛唐边塞诗,一般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和文明自豪感,后人往往就此肯定甚至推崇这些作品。这种价值观,若站在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未必正确。即便是站在盛唐时代,恐怕也不能获得完全赞同。在这个问题上,杜甫在当时是一个异类。人们很久就有疑惑,在边塞诗创作风行的盛唐,杜甫何以很少写这样的作品?即便是为了平定安史叛乱而勉励人们从军,杜甫的笔端也看不到冠冕堂皇的陈辞滥调。也许有人会说,杜甫没有从军和使边的经历。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杜甫为什么没有从军和使边的经历?也许有人会说,没有人引荐他。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是没有人援手,还是杜甫自己始终拒斥军幕?答案是后者。天宝十三载(754),杜甫作《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表达了入幕的愿望,这大约出于“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情势之下的不得已,[1]当不能概括杜甫平生的追求。同为伟大的诗人,李白曾经梦想“沙漠收奇勋”,但推重李白的杜甫却感慨“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而没有相类诗篇流传于世。他留下的诗多见对“觅封侯”的忧虑,如夔州所作《复愁十二首》其六:“胡虏何曾盛,干戈未肯休。闾阎听小子,谈话觅封侯。”杜甫选择拒斥从军入幕,决定于他的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他超出时代的政治情怀和思想境界。
后人常因杜甫诗见于唐人选唐诗者少,尤其“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的《河岳英灵集》对他的有意忽略,便认定杜甫没有当世之名,这一认知或有大误。事实是,杜甫并不是没有当世之名,只是他不受当世推重而已。杜甫的诗之所以不受当世普遍的重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杜甫过于积极进取,而不能有所不为,在他那个时代应该最独特。他得官以后才约略看清自己,“独耻事干谒”等诗句就传达了他的自我反思。但即使如此,尽管有所不为了,他仍然继续坚持理想的追求,这也是独特的。殷璠论刘眘虚诗“并方外之言”、张谓诗“并在物情之外”、王季友诗“远出常情之外”、綦毋潜诗“善写方外之情”、祖咏诗“调颇凌俗”,由这些评语可知,盛唐大诗人普遍进退自如,杜甫则有异于此种时代风尚。杜诗之未能见重于当代,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杜甫生长于他的时代,又超然于他的时代。杜甫自云:“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可以说大部分情况之下,杜甫都是以俯视的姿态面向他的时代的,他是高出尘世间的。任华寄杜甫诗曰:“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韦迢留别杜甫诗曰:“大名诗独步。”郭受寄杜甫诗曰:“新诗海内流传遍。”杜甫诗曰:“文章有神交有道”,“每语见许文章伯”,“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政术甘疏诞,词场愧服膺”,“才微岁老尚虚名”。这些可以说明杜甫的文章盛名并非受赐于中唐韩愈、元稹和白居易或宋人,而是他自己的气象造就的。综合任华的赞羡和杜甫其他诗篇的自述来看,在诗艺上,杜甫善于广泛学习借鉴飞腾的前辈和所有同时代大诗人的创作经验;在思想上,他却是一个逆时代而动的人。个中原因不易参透,杜甫的价值选择可能植根于他追逐政治理想的坷坎遭遇,更可能因缘于他理想主义者的天机。他的《前出塞》和《后出塞》组诗,尤其《前出塞》,以批判战争为旨归,与以王昌龄、岑参等人为代表的盛唐边塞题材创作相照映相对立,是杜甫与时贤之间在社会政治问题和思想境界层面的直接对话。杜甫诗曰:“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战争的胜利鼓动了时人的热情,造就了后人景仰的极盛时代,但战争的失败和边将的反叛,恰恰彻底摧毁了盛世,这是大唐盛世政治生态无可自决的死结。杜甫对唐代开边战争的认识,体现了他迥出于时代的政治见识。这一政治见识,无疑是现代性的,具有人类文明普适性的大意义。
二 杜甫的政治批判与道义坚持
鲁迅曾说,中国古代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有人戏仿说,中国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想做奴隶而不得,另一种人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杜甫不属于鲁迅所说两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就此而言,他受赐于那个伟大的盛唐时代。从其“致君尧舜”的自许,献赋所见的讽谏和期待以及“牵裾惊魏帝”等不计现实利害的实际作为来看,杜甫不属于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如陆游《东屯高斋记》所言,杜甫的现实理想是“少出所学以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故无论中年“朝扣”“暮随”之干谒、晚年无可奈何之奔走,杜甫始终保持着政治引领者和政治批判者的独立姿态。在杜甫心目中,他所秉持理想的“道”是优先的,是凌架于世俗的“势”之上的。他不是专制时代常见的愚忠者,在道与势的选择上,他继承发扬了先秦儒者的独立精神,他就是“圣贤古法则”在后世的“传”者。赵次公为张焘重修草堂并刻诗碑所写《杜工部草堂记》称杜甫“出处每与孔孟合”是有道理的。明初宋濂《杜诗举隅序》则批评杜诗注者曰:“骋新奇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而为说。”宋濂意在批评注杜家求新奇者之迁就穿凿,亦在批评他们以杜诗“无非忠君爱国”的阐释思路。
乾元二年(759),杜甫作《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曰:“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由此诗可以略见肃宗即位后朝中政治生态的不良倾向,“莫使众人传”当然也隐含了杜甫对自己创作的反思和警醒。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孱弱的朝廷,一个不够健康的政治体,经不起批评,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甚至不允许腹诽,但他似乎没有向此种不良的政治生态完全屈服。贬官华州,最终辞官,可能都与他的不屈服有关,而此后杜甫诗中的政治批判,更多体现了他的价值承担和道义抉择。孟棨单独拈出杜甫流离陇蜀的诗篇为“诗史”,为“推见至隐”之作,当对此有深切了解。广德元年(763),杜甫作《泛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曰:“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大历三年(768),杜甫作《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曰:“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对返京和京中友人说不要轻易传布自己的诗,这说明杜甫对自己流离陇蜀以后所作“推见至隐”的批判诗篇颇有顾虑。在此之前,杜甫没有这种顾虑。天宝九载(750),杜甫作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曰:“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此诗透露的是对自己“佳句”的傲然自得。两相比照,不难发现,对上述价值选择,杜甫是有所忧惧的。但他忧惧的不是个人世俗利益得失,而是世俗政治最终不会选择自己担当引领者。前引衡州判官郭受寄杜甫诗曰:“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 “流传遍”,宋本《杜工部集》卷一八作“流传困”。杜甫酬答诗曰:“才微岁老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详绎郭、杜二诗的情绪,似宋本“流传困”之“困”字为优。也就是说,杜甫之多年“卧病江湖”与其诗作流传而带来的世俗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或有重大关系,其“推见至隐”的诗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晚年困顿江湖的遭遇。俗语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杜甫明知触犯专制政治的忌讳,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价值选择,无疑他是一个有大勇气的古代知识者。
人类社会是多元的,历史上举凡伟大的人物,其行为、思想和历史影响也是多元的。饥寒表达和社会批判,是杜诗当中一而二、二而一的两大主题,是理解杜甫的关键。所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啼饥号寒是先秦儒者有意搁置的问题。杜甫则不同,他要表达,他要不停地诉说。个体生存和道义持守在他这儿是等价的,这是杜甫对先秦儒学的发展。杜甫终生都在表达他的饥饿与寒冷,一如惠洪《次韵谒子美祠堂》所言,“死犹遭谤诬,谓坐酒肉馑”,“牛酒饫死”的“故谤伤”之言显系由此杜撰而来。因缘幼子饿死、娇儿恶卧的惨痛经历,因缘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杜甫诗中时时出现的饥寒表达,更多可能是他对内心不能饱于仁义的隐喻。王安石《子美画像》“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杨甲《与客游沧浪亭分韵得一字》“岂无独往愿,冉冉饥冻逼”、李纲《杜子美》“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喻汝砺《晚泛浣花遂宿草堂》“云何尝念饥,零落在道旁”、戴复古《杜甫祠》“干戈奔走际,道路饥寒状”,大约都读出了杜诗饥寒表达的深意。因此,不苟免于饥寒,自当视作杜甫主动选择承受的此世大苦行,他是以一己之遭际,关联着天下寒士众生之遭际;以一己之饥寒,关联着天下寒士众生之饥寒。这无疑表征了杜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恒久道德冲动。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诚如洪业所云,“But poetry was,to him,only an advocation,not a vocation”[2],杜甫的平生志业不在诗,诗对他来说并非天赋职任,不过是激发而为。杜甫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单在诗,更在他所持守的道。杜甫同时的任华寄诗曰:“而我今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宋初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曰:“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颠沛寇虏,汩没蛮夷者,屯于时耶,戾于命耶,将天嗜厌代,未使斯文大振耶。虽道抑当世,而泽化后人,斯不朽矣。”宋绍兴十年(1140),成都知府张焘重修增饰杜甫草堂,赵次公作《杜工部草堂记》曰:“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乾道七年(1171),陆游任夔州通判,受杜甫故居东屯高斋现主人李襄的邀请,撰《东屯高斋记》,其中论杜甫晚年遭遇曰:“去国寖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以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清初宋琬《祭杜少陵草堂文》曰:“天既赋公以稷契之才,不使之一日立朝廷之上,而穷愁播越,终其身老,道路以凄其。”屈大均《杜曲谒杜子美先生祠》有曰:“稷契平生空自许,谁知词客有经纶。”以上诸家都意在说明杜甫有其道而无其时。
杜甫不只是一个政治和人性的批判者,作为寄身于体制之中的利益既得者之一,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善建者。杜甫自云,“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但当时便“取笑同学翁”。苏轼《评子美诗》曰:“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详绎其语,东坡或因个人之高位而深知稷契之不易甚至不可能,对杜甫是否真的能够成为稷契般人物,未置可否,但他肯定杜甫具有此种潜质。大历二年(767),杜甫作《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曰:“勉励疲钝,伏扬陛下之圣德,爱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简易,间之以礼乐,均之以赋敛,终之以敦劝。”按此即杜甫设想自身为宰辅之后的政治举措,苏轼对此显然是认同的。陆游《读杜诗》曰:“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方回《秋晚杂书三十首》其十九:“窃尝评少陵,使生太宗时。岂独魏郑公,论谏垂至兹。”放翁肯定了他心目中杜甫的政治秉赋,却也道出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后人大多仅仅以将杜甫视作诗人。《朱子语类》卷一四 载朱熹曰:“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此论于杜甫之政治才能提出疑问,但肯定了杜甫持守道的品格。清同治内阁中书谢章铤为西安杜公祠所写《重修杜工部祠碑》曰:“子美始善房琯,继善严武,稍为委蛇,皆足以取世资。乃何以每饭不忘君如此,而老大意转拙又若彼也?”在谢章铤看来,杜甫之政治失意,缘于他不能与俗委蛇。清初宋琬为秦州李杜祠所写《二绝碑赞》表彰杜甫曰:“猗嗟先生,志侔稷契,遘乱播迁,身穷道洁。”诚如杜甫离蜀之前《三韵三首》其三所云,“名利苟可取,杀身傍权要,何当官曹清,尔辈堪一笑”,这正可说明杜甫政治失意的根源在于他对理想政治的期待和对道的持守。《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陈绝粮,一度似乎对自己执守的“道”产生了疑惑,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本质上说,杜甫政治失意,问题不在杜甫,而在世俗政治。《新唐书·杜甫传》最早评判说:“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话属人云亦云的泛论,其实不全对。杜甫在人际交往上可能存在过于清狂之弊习,然其政治见识是可以肯定的。诚如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杜文注释”所云:“其代为表状,皆晓畅时务,而切中机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相信正常的情况下,杜甫居官期间对与叛军如何作战以及在蜀对如何区处吐蕃侵边问题的建议大多是可行的[3]。洪业将李白和杜甫作比较时说:“Li Po was essentially an escapist.Tu Fu was at heart a reformer.The escapist would naturally take human relationship more lightly than the reformer.The best reformer will not allow his affection to wane simply because it is not requited.”[4]这是极高明极具穿透力的评价,李白是遁世一派,杜甫则属于重建秩序的一派。可惜的是,历史未曾给予杜甫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三 杜甫遗迹及《杜甫遗迹研究》的意义
杜甫生长、干谒、居官的京洛一代和漂荡迁移的西南湖湘地区,虽经历史淘洗,迄今仍保留了许多他的遗迹。这在众星琟璨的唐代诗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些遗迹也正是杜甫精神一千多年感召力的体现。明蜀献王朱椿重修成都草堂,并作《祭杜子美文》,曰:“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往而不在焉。”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收宋元之际逸士宋无(误作旡,无有《翠寒集》,收此诗)《杜工部祠》,按语曰:“夫唐代诗人,何啻千辈,独少陵忠义之气,足以感发人心。故足迹所经之地,千年祠宇,今古留传,此诗人之另辟乾坤者。”
杜甫遗迹大要可以区别为两类:一是杜甫昔日登临居止和魂魄憩息之所,二是后世兴建的楼阁、亭台、草堂、书院和祭祀杜甫的祠堂等承载一定文化功能的纪念场所。杜甫奔走半天下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他以如椽之笔书写了之前未曾发现的自然美,其中最突出的是杜甫秦州、同谷之行所留下的诗篇。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訔撰《编次杜工部诗序》曰:“时危平,俗媺恶,山川夷险,风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概见,如陪公杖屦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清顺治十三年(1656),宋琬主持重修了秦州天靖山李杜祠,并将杜甫秦州、同谷之诗刻石于祠中。宋琬《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跋》曰:“夫陇山以西,天下之僻壤也。山川荒陋,冠盖罕臻,缙绅之士,自非官于其地者,莫不信宿而去,驱其车惟恐不速。自先生客秦以来,而后风俗景物每每见称于篇什。”乾隆六年(1741),牛运震主持重修同谷栗亭杜公祠,其《杜公祠记》曰:“子美杖履遨游万里,籍以发山水之奇迹。”这些表彰既突出杜诗陇西之自然书写,也是为了弘扬地方文化。光绪甲午(1894)二月初七孙宝瑄论杜甫《瞿塘两崖》等诗曰:“天地间一名一物,一形一色,莫不有真精神、真趣态。或过焉不留,或日当其前而不知,或知焉而不能言,多矣。而惟诗人能刻划之,形容之,使天地间名不虚名,物不虚物,形不虚形,色不虚色。故画家能画其迹而已,而诗能画其神。有诗笔到画笔不到者,未有画笔到而诗笔不到者。且画与诗其传世之远近何如耶?画依乎楮墨,虽有明绘,而雕残剥蚀,渐久即化为乌有,而诗则火不能燔也,水不能濡也,虫不能蚀也,风霜不能侵也。遂使天地间真精神、真趣态,偶一呈露,即长留于人间。噫嘻!此诗之可贵也。”[5]
杜甫的人格精神见于他的诗篇,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深切领会杜诗,故散见各地的杜甫遗迹,为一般人了解亲近杜甫精神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司马迁到鲁国,“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祗回留之不能去”,由是感叹“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唯“至圣”孔子当时不荣,没亦不灭。司马迁到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由上面约略的例举可知,司马迁观孔子屈原遗迹的留连、怀想和景仰,在历代文士寻访观览凭吊杜甫遗迹而留下的碑记、诗歌等文字中常常能见到。
大多杜甫遗迹与杜甫直接相关,也有不少遗迹则是由其他遗迹和杜甫行踪的传说衍生而来。如明代采铜川羌村,明延安杜甫川,清延安杜公祠,清乾隆仙嘉岭东南六十五里的杜甫草堂、子美村、子美泉。历史上各地对杜甫遗迹诸如出生地、卒葬地等的争夺,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仿佛拥有杜甫遗迹便拥有了某种潜在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源,此种争夺应视作杜甫在后人精神世界巨大影响力的投射。各类杜甫遗迹之兴建重修,显然是为了发扬杜甫精神在一定时代一定地方当前的文化意义。也正因为此,时过境迁,承载过去时代文化诉求的大部分杜甫遗迹往往会屡有兴废。改朝换代时如此,即便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亦是如此。明洪武二十六年,蜀王朱椿重修成都杜甫草堂,方孝孺为作《成都杜先生草堂碑》曰:“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废于兵也盖久。大明御四海,贤王受封至蜀,以圣贤之学施宽厚之政。……复谓先生为万世所慕者,固不专在乎诗,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睹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为心,咸有愿学之志,则草堂不可终废。”朱椿希望重修草堂能够激发士君子“愿学之志”,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振兴蜀地文化。
考察历史上中国各地的杜甫遗迹,会发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规律,即杜甫遗迹往往兴废无常,建而又修,修而又废,废而又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乱,尤其是易代之际,而其他时段则主要因为人们疏于守护和管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像杜甫这样代表中国人共同心灵祈向的伟大人物,其遗迹何以有如此遭遇呢?深层原因大概是,如杜甫当世所感慨的那样,中国人的生存太苦,太酸辛。一般人往往为了生计或理想而奔波劳顿,对于与己生存不甚相关的外物无暇顾及。古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实我们的内心都跟杜甫一样,期望有一个常在的道。
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平庸者。杜甫之所以深得后世崇敬,也因为他虽是一个伟大的人,却并没有抛弃所有的平庸,没有藐视平庸的众生,没让我们觉得他高在云端。按照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念,利用传统为当下服务属于“质朴的幼稚”[6]。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在西方,这种“质朴的幼稚”已经消失。然而我们看到,在古往今来关于杜甫遗迹的碑记诗咏中,杜甫本人不再重要,大多数情况下,他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甚或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杜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杜甫思想的实际状况,杜甫本人的行踪,甚至杜甫诗歌有时也会被人们断章取义地加以阐释。因为杜甫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无论历史如何流转迁换,无论各处杜甫遗迹如何毁弃兴废,杜甫胸怀中华文化、高扬独立人格和批判意志的伟大精神,势必永远鼓舞一代一代中华儿女,推动中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总体来看,王超《杜甫遗迹研究》能够综合文献资料、实地考查和出土文物,考证辨析真伪,又能跳出一般真伪纷争之外,发掘大的文化意义。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综合传世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所得,力求探明全国杜甫遗迹的历史变迁,发掘各地杜甫遗迹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意义。详考各地重要杜甫遗迹的历史变迁,颇能见出不同时代的文化风向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状貌。政区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通常关注的是一个较大地理区域的历史变迁,但对成都草堂、夔州相关遗迹的考察,似可名之为微观地理学,这是王超《杜甫遗迹研究》一个极有意义的贡献。
古人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超的《杜甫遗迹研究》与《访古学诗万里行》等以踏访杜甫遗踪为追求的研究路径不尽相同,他以行万里路的田野考查为基础,而更重视发掘杜甫遗迹的所有文献和文物资料,努力探明各处遗迹的始建、兴废、改造、迁址及其与一定时代地方文化和整体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之前杜甫遗迹研究基本上是地方性的,局部的,对不同地区的杜甫遗迹很少有整体统一的综合研究。地方性的观察视角,一般多着眼一时一地,从而又导致历史地理的疏失。王超《杜甫遗迹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不少有意义的历史地理考据学案例,其中对梓州和夔州两地杜甫寓居地具体位置的考察最为精彩。可以说,类似研究从历史地理变迁的视角重新审读文献记载,纠正了一般地方性的感性认知。其意义当然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对准确理解相关杜甫诗是不可或缺的。
生老病死是人类共同的对手,也是人而为人的必然。杜甫没有逃过这个必然,但他用自己的诗和精神超脱了老病,超越了生死。2014年王超开始读博,原本我希望他能以盛唐文学史为选题范围,尽可能提供一部足以服古人之心的盛唐文学的真实立体的画卷。他略有畏惧,因为唐代文学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最为中心的领域,盛唐文学则是唐代文学的中心,代表了唐代文学的高度,研究最为充分,想要形成突破不容易。最终王超遵从自己的志趣和知识积累,选择了杜甫遗迹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这个题目我当初感觉只是个题目,一则担心胜义无多,一则担心这不能导入杜甫研究和唐代文学的最核心地带。随着论文研究的展开,我再没担心论文,而只是担心他的身体。王超为人骨骾多气,对学术和社会问题也极其敏感。他之喜欢杜甫,大概也是因为与前圣的某些心灵相通。在论文写作的几年里,他要做田野调查,他要翻检有唐至近代的大量相关文献,他要把思考组织成文,同时还要发表获得博士学位必须的科研成果,其中艰辛,可想而知。记得一位朋友说过,对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我们感同身受,却无可奈何,爱莫能助。诚然如此,我们无力改变不断变幻的现实,唯有调整自己。《杜甫遗迹研究》一书试图为杜甫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相信未来王超能够在顾惜健康的同时,取得更多的优秀成果。
[1]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82.
[2]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6.
[3]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61.
[4]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88.
[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40页。
[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导言》,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