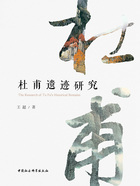
绪论
杜甫是文学史上最受后世推崇的诗人,今人更将其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一生经历丰富,早年生活在洛阳一带,青年时游历齐赵,而后旅食长安。安史乱起,杜甫为躲避叛军,偕家人客居鄜州,只身投奔肃宗后,任左拾遗。又因房琯案牵连,被贬华州,不久辞官,与家人一道经由秦州、成州等地,最终定居成都。在成都安度数年后,又再次踏上奔波之途,先后客居梓州、阆州、夔州、潭州、衡州诸地,最终客死于岳州一带。杜甫逝世四十余年之后,其孙杜嗣业才将其灵柩迁葬偃师祖茔,最终落叶归根。由此可见,杜甫生前身后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是多么广阔。
一 杜甫遗迹的内涵与外延
杜甫逝世之后,其文学才华、高尚品格逐渐受到后世文人、官员的重视与褒扬,寻访杜甫遗迹、创建纪念建筑的文化活动渐次展开。自宋代以来,各地或是依杜甫旧居遗址兴建祠堂,或是对杜甫墓冢屡加修葺,或是以杜诗命名和构筑亭台楼阁等纪念性建筑,甚至根据无法确切考证的传说故事为杜甫兴建祠宇、坟墓。
杜甫遗迹的概念,若就狭义而言,应当是杜甫亲自营建的住所,以及后人为杜甫修葺的坟墓,这是最为核心的杜甫遗迹。但推而广之,后人又会在杜甫旧居、坟墓的范围之内,或是杜甫游历所经之地,创建祠堂等纪念性建筑,以便官员及仰慕杜甫的各界人士瞻仰、祭祀,形成与杜甫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故而,就广义而言,杜甫遗迹不仅应当包括杜甫旧居及坟墓遗迹,还应当包括后人为纪念杜甫而建造的祠宇、亭台楼阁等与杜甫有密切关联的历史文化遗迹。
与杜甫相关的旧居、坟墓、祠宇、亭台楼阁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从表面上看,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文物,即便有些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仍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它们的身影。但如果将杜甫遗迹看作是没有生命的历史遗留,那就有失偏颇了。一方面,这些杜甫遗迹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后人为纪念杜甫,不断加以保护、兴建、维修、扩建的结果,其中蕴含着古人的所思所想与艰辛历程;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后人不断的保护、修葺过程中,形成了碑刻、游记等文献记录,为我们了解杜甫遗迹的变迁历程、理解杜甫遗迹丰富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这些文献虽说附着于杜甫遗迹之上,但相较于物化的遗迹本身,更具文化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笔者将杜甫遗迹界定为与杜甫相关的旧居、坟墓、祠宇、亭台楼阁等历史文化遗存,以及相关传世文献的总和。这其中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也有着灿烂夺目的精神文化世界。因此,笔者期望以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物质遗迹的变迁与演进历程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古人在寻访、保护、创建、维护杜甫遗迹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揭示杜甫遗迹所蕴含的厚重文化内涵。这不仅是对唐代以来杜甫文学形象演变过程的研究,也是在更广阔的视域之下,对后世杜甫接受历程的全新揭示。
二 杜甫遗迹相关传世文献概述
杜甫去世数十年后,已有杜甫墓志铭、传记、故事流传开来。晚唐五代之际,吟咏成都草堂、耒阳杜甫墓的诗篇亦是层出不穷。自北宋王洙开始,搜集杜诗、研究杜诗、“千家注杜”渐渐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同样自宋代以来,为杜甫修建祠宇、以杜甫及杜诗命名纪念性建筑,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至明清时期,地方官员、文人注重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也就引发了在杜甫各寓居地兴建祠堂的热潮;加之对杜甫病卒之地、旅殡之地、卒葬之地都存在不同的观点,故而造成偃师、巩义、耒阳、平江均有杜甫墓的情况,这些争议一方面形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局”,另一方面也为杜甫遗迹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纷繁复杂而又层次多元的文献资料。现以时代为序,将不同历史时期的杜甫遗迹文献的特点概述如下。
晚唐五代文献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是元稹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请,为杜甫撰写的墓志铭,可谓是记述杜甫生前身后事的权威文献。其二,唐诗中吟咏杜甫遗迹的篇章。如唐人赵鸿《杜甫同谷茅茨》,吟咏杜甫成州故居;又如雍陶《经杜甫旧宅》、郑谷《蜀中三首》之二吟咏杜甫成都草堂;再如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裴说《经杜工部坟》、齐己《次耒阳作》,吟咏耒阳杜甫墓。其三,正史及笔记中的记述。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后晋刘昫《旧唐书》收录的杜甫传记都有杜甫酒醉饱食、卒于耒阳的记载。
两宋文献对于杜甫遗迹的记述,也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宋本杜诗集注的突出价值。宋人重视杜诗、欣赏杜诗,已有“千家注杜”之说。注释杜诗,自然要解读杜诗中的地名、人名,这就需要指出、点明杜甫流寓所经、故居遗址的大致方位或具体位置。就目前所见,较早最具代表性的是两种注本:一是宋人吕大防、王洙、赵次公等人注解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是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尤其是宋刻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在全书卷首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序》一卷,将当时所见的杜甫诗集序言、题跋,杜甫墓志铭、两《唐书》杜甫传记等文献搜罗齐备,为今人研究杜甫遗迹提供了宋代保留的文献资料。
其二,宋人乐于编纂杜甫年谱。吕大防《杜诗年谱》、赵子栎《杜工部年谱》、蔡兴宗《杜工部年谱》、鲁訔《杜工部诗年谱》、黄鹤《杜工部诗年谱》等五种宋代杜甫年谱流传至今,虽说详略有别,但其中均有杜甫遗迹的线索,为后人追寻杜甫行踪指明了基本路径。
其三,散见于宋代文人文集、总集及地理志中有关宋代杜甫遗迹的记述。如北宋人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见其所著《嵩山文集》;赵次公、喻汝砺同题《杜工部草堂记》见诸南宋庆元年间编成的《成都文类》;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赵师古《题杜工部墓祠序》则见明清方志传承收录。此外,《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中亦有关于杜甫故宅、杜甫墓的相关记载。
明清文献关于杜甫遗迹的记述极为丰富、蔚为壮观。这既有地方文化蓬勃发展、追慕前贤的因素,也由于明清两朝距今尚不算久远,保存至今的文献总量庞大,其中有关杜甫遗迹的记述自然也会较唐宋呈现出倍增的现象。明清文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以地方志书为代表的地方文献中对杜甫遗迹与杜甫崇祀活动的记载不断涌现。如西安杜公祠自明嘉靖初年创建以来,历代重修杜公祠的历史文献大多完整的保存在明嘉靖《陕西通志》、万历《陕西通志》、清康熙《咸宁县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咸宁县志》之中,又见于《关中两朝文钞》等地方艺文集的收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石刻文献的留存,一些重建、维修杜甫祠墓的文献虽然未见地方志书收录,但仍有碑刻文献留存于相关历史遗迹周围,同样作为文物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明清两朝重修栗亭杜公祠的文献、重修偃师杜甫墓的文献大多以碑刻的形式保存至今。
上述对唐宋明清各个历史时期杜甫遗迹相关文献的概述,是就各自独立的历史时期的文献特点而言,这其中当然也存在一些文献互相交叉的情况。如《新唐书》中杜甫传记就是出自宋人之手;又如陕西鄠县渼陂有空翠堂,堂名源自杜诗,创自北宋宣和年间,并有碑刻流传,但我们今天看到的《空翠堂记》则是明人于隆庆年间重新刻立的。即便是文献资料丰富的明清时期,也存在对杜甫遗迹研究进行排比、拼图的问题。例如成都草堂久负盛名,但要厘清历代重建、重修草堂的文化传承关系,必须将地方志书中的修葺文献、文人文集中的草堂游记、现存碑刻文献,甚至于出土文献,一同总和起来、通盘考量,才能基本上还原唐代以来成都草堂变迁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脉络。
简而言之,与杜甫遗迹相关的历史文献唐宋时期相对较少,记述不多,且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至明清时期呈现出体量巨大、头绪繁多、排比困难、冗繁杂乱的特点。而明清时期这些互相矛盾的文献记载,究其源头又是由记载不详的唐宋文献所引起的。如偃师与巩县的杜甫归葬地点之争、耒阳与平江的杜甫旅殡地点之争,皆是对唐宋以来文献的不同解读,引申、发展而来的典型例证。因此,对基础文献的解读,是本书的重中之重。
三 杜甫遗迹研究相关成果综述
有关杜甫遗迹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至今未有系统性的研究问世。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附着于杜甫及杜诗研究中的杜甫遗迹研究
杜甫其人与杜诗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知凡几。在研究杜甫生平事迹、行踪路径、诗歌艺术特色、系年考辨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杜甫遗迹的问题,或是将现存的遗迹作为杜甫旅行所经的重要物证。因此,针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中,会出现将杜甫遗迹作为杜甫研究、杜诗研究附着物的情况。
这一研究范式由来已久,自宋人“千家注杜”以来,历朝历代与杜甫遗迹相关的研究一直作为集注杜诗的内容或补充而存在。例如上文已列举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杜工部草堂诗笺》等宋人集注、笺注以及各家年谱等,兹不赘述。
近现代以来,亦有许多知名学者在研究杜甫、杜诗的过程中,将一些研究杜甫遗迹的成果融入著作、论文之中。如洪业于1952年出版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1]一书中就针对杜甫旅殡平江之说,认为平江杜氏家族所藏杜甫至德二载诰敕为伪造。再如陈贻焮所著《杜甫评传》[2],以页下注释的形式,将杜甫同谷旧居、成都草堂的基本线索、位置所在以及争议分歧予以介绍说明,并对杜甫卒葬耒阳说予以否定,而对于杜甫是否卒葬平江则采取了严谨的态度,只沿袭元稹“卒于潭岳之间”的旧说,未敢有定论。又如中国台湾学者陈文华在其专著《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3]中详细研究考辨了杜甫家世、生平事迹异说等方面的内容。专著针对杜甫耒阳“饫死说”“溺死说”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考辨,并指出此前认为是唐人李观撰写的杜甫《遗补传》实为宋人李观所撰,这其中亦涉及对于唐宋以来耒阳杜甫墓的研究。再如傅光在其专著《杜甫研究(卒葬卷)》[4]中首先讨论了杜甫逝世时间的各种观点,认为杜甫确于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并且葬于耒阳。当然,傅光的观点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
除上述著作以外,有更多论文在讨论杜甫与杜诗的过程中,涉及杜甫遗迹问题,在此仅列举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针对杜甫卒葬地是偃师还是巩县的争议,有霍松林《杜甫与偃师》[5]。针对杜甫湖南诗的系年编次研究,也涉及杜甫岳州、潭州、衡州、耒阳诸地行踪、遗迹的问题,如魏泽一《试论杜甫在湖南作诗的编次问题》[6]、樊维纲《杜甫湖南纪行诗编次诠释》[7]、毛炳汉《杜甫湖南诗新的总编次》[8]、文正义《杜甫湘行踪迹及其死葬考》[9]、李一飞《杜甫流寓湖南行事考辨三题》[10]、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11],以及丘良任《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12]、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13]。上述论文除李定广赞同傅光观点,认为杜甫卒葬耒阳之外,其余学者都对卒葬耒阳说持否定态度,亦对杜甫旅殡平江说持谨慎态度。师海军《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14]主要讨论安史乱起后杜甫避乱鄜州行程问题,其中亦涉及杜甫鄜州羌村故居问题。聂大受《杜甫陇右行迹及纪念物探》(上、下)[15],专述杜甫秦州、成州行程路线,亦介绍两地杜甫遗迹问题。
(二)基本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
上文已经说明,明清以来有关杜甫遗迹的文献多依靠地方志书、地方文献总集以及石刻碑文的记载。如今《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地方志书大量影印结集出版,为杜甫遗迹文献的查找与检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研究杜甫遗迹的来龙去脉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仍有不少碑刻文献不见于明清以来地方志书的记载。这就需要借助于石刻文献的著录整理。
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主编《洛阳明清碑志·偃师卷》[16]将偃师杜甫墓相关碑文拓片及碑文收入书中,对研究偃师杜甫墓的情况大有裨益。刘雁翔《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17]收录了天靖山李杜祠及南郭寺杜公祠的碑刻文献,为研究秦州杜甫遗迹的演变历程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赵逵夫主编的《陇南金石录》[18]收录了成县(成州同谷县)与徽县栗亭杜公祠的碑刻文献,为研究成州杜甫草堂以及徽州栗亭杜公祠的创建、维修情况提供了便利。吴敏霞主编的《长安碑刻》[19]著录了西安杜公祠创建以来的若干碑刻拓片及碑文;刘兆鹤、吴敏霞编著《户县碑刻》[20]著录了宋明以来创修渼陂空翠堂的石刻拓片及碑文。李霞锋《成都草堂古代碑刻初考》[21]著录了成都草堂所藏碑刻文献。这些石刻文献的著录整理可补地方志书中艺文之缺漏。
上述地区笔者虽然都曾亲自前往考察,并逐字逐句抄录了不少碑刻文献,但匆匆探访之际,面对数量众多的碑刻文献,难免存在遗漏与辨识困难的遗憾。加之碑刻由于自然、人为因素的损坏,上述整理成果在著录、释文过程中也常出现识读困难、文字缺漏、断句错误等问题,但瑕不掩瑜。简言之,碑刻文献的整理与发表,为杜甫遗迹文献的全面搜集与整理提供了方便,并为杜甫遗迹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各地杜甫遗迹研究取得的成果
由于杜甫遗迹分布在多个省份、地区,自宋代之后,逐渐演变成各地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全国各地杜甫遗迹研究的成果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而这其中的重点与热点就是成都草堂。目前所知,对于成都草堂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民国三十二年(1943)吴鼎南编著的《工部浣花草堂考》(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出版发行)一书就成都草堂的建筑格局、草堂历史变迁、草堂故事传说、草堂碑碣存目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论述。至20世纪80年代,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都草堂纪念馆共同创刊出版《草堂》期刊(《杜甫研究学刊》前身),强力推动了以成都草堂为中心的杜甫遗迹研究,如郭世欣《成都草堂遗址考》[22]、王文才《冀国夫人歌词及浣花亭考》[23]、吴鼎南《略谈古草堂、梵安两寺及杜甫草堂的位置》[24]、周维扬《从草堂唐碑出土略谈古今草堂寺之争》[25]、陶喻之《浣花古刹考略——唐益州正觉寺钩沉》[26]、赵晓兰《〈成都文类〉中的杜甫草堂》[27]、刘洪《再论浣花夫人、浣花祠与杜甫草堂》[28],注重于对唐宋时期成都草堂历史的考索与辩证,试图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多方位、多视角复原该时期草堂的地理位置、解析时人尊杜思想史等方面的问题。
除成都草堂遗迹研究之外,又有杜甫纪念馆《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29]、袁仁林《杜甫寓夔故居考》[30]、王大椿《杜甫夔州高斋历代考察述评》[31]、江均涛《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32]10等成都周边杜甫遗迹研究文章发表。
杜甫遗迹研究另一个争讼的焦点是杜甫葬地问题,涉及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研究文章数量也很可观,现将其中代表性论文综述如下。霍松林《杜甫与偃师》[33]1、郑慧生《杜氏家族与偃师杜甫墓地》[34]12、南新社等《〈杜甫终葬巩县说〉质疑——与李丛昕先生商榷》[35]13认为应当遵从元稹所撰杜甫墓志铭的记述,杜甫归葬偃师无疑议。傅永魁《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36]、李丛昕《杜甫终葬巩县说——兼向霍松老请教》[37]、刘玉珍《诗圣杜甫和巩义杜甫墓》[38]则认定巩县杜甫墓是真墓。张中一《巩县与偃师杜甫墓辨析》[39]否定了偃师与巩县杜甫墓的真实性,樊维纲《杜甫后裔流域平江事考索》[40]、董希如《平江杜甫墓研究述评》[41]则认定平江杜甫墓才是杜甫最终归宿。唐人认定的耒阳杜甫墓则支持者寥寥。
此外,秦州、成州杜公祠也是一处研究热点。吕兴才《杜甫与徽县》[42]、刘雁翔《杜甫陇上萍踪》[43]均有专门章节以描述性的文字介绍栗亭、秦州、成州等地杜甫遗迹,又有蔡副全《成县杜甫草堂历代诗碑考述》[44]、《栗亭杜少陵祠考述》[45]10等专业论文面世。此外,尚有周维扬、丁浩《杜甫草堂史话》[46]1、邓荣生《杜甫在平江》[47]12等普及性读物出版面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1980年萧涤非先生带领《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两次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南等地,对有关杜甫的行踪遗迹及影响做了一番初步的考察访问。1982年又以《杜甫全集》校注组的名义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该书以游记的形式,将沿途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其中留下很多杜甫遗迹的线索和文献提示,由此不得不感慨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学养与极端负责的治学精神。此书的研究范式也指引着当今学者,如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48]即可视为对《仿古学诗万里行》的继承与发展。
通过对上述杜甫遗迹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研究成果的地域失衡。杜甫遗迹分散于全国各地,其研究成果尤以成都、秦州、夔州、偃师、巩县、平江等地为重点,而对于杜甫长期生活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周边鄠县、鄜州等地的遗迹尚无高水平研究成果面世。
其二,研究成果中的无意义争讼。学术研究成果有争议、有商榷固然是好事,但是在围绕杜甫墓真伪的争论中,只强调自己的证据,一概否认他人的证据,这种学术倾向较为突出,因此形成了长期争讼不绝的问题。
其三,研究者不熟悉明清文献及历史地理知识。杜甫研究者一般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区域史等研究领域,而现存有关杜甫历史遗迹的文献记录多出自明清两朝地方官员的手笔。研究者大多对明清历史和明清职官制度较为生疏,经常难以准确考辨人物生平,揭示文献的深层涵义。历史地理知识的欠缺是限制研究水平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研究者的历史地理知识较为有限,因此时常出现对杜甫遗迹的表述不够精确、方位变迁把握不够准确,甚至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现象亦时有发生。
四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现存杜甫遗迹数量多、分布广,与杜甫遗迹相关的传世文献较为充裕,个别地域的杜甫遗迹研究成果丰富的基本现状。因此,本书的写作秉承了以下三点研究方法。
第一,坚持田野调查法。尽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式了解每一处杜甫遗迹的地理位置和现状,亲自搜集最准确的第一手文献。本书中研究的绝大多数杜甫遗迹,笔者曾赴实地考察,现场识读、抄录现存的碑记、石刻文献。鄜州、秦州、巩县等地区存在多处杜甫遗迹,或遗迹本身的地理方位出现过多次变化,容易使读者产生混淆。对此,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在文中添加了遗迹方位示意图,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遗迹方位的历史变化和多处遗迹之间的方位关系。一些杜甫遗迹中的碑记、石刻文献,前人已有整理研究,但碑文文字及句读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笔者在引用文献时,以实地抄录内容为准,避免了二手文献引发的歧义。此外,坚持实地考察的方法,决定了本书基本以杜甫行迹顺序为线索探寻杜甫遗迹,这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萧涤非先生为代表的《杜甫全集》校注组所著《访古学诗万里行》的致敬。
第二,坚持实证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做好文献研究。做好基础文献的搜集与解读工作,最大限度的占有杜甫遗迹相关文献,力求在竭泽而渔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杜甫遗迹研究成果存在互相矛盾、前后抵牾的情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要将杜诗、历代注解、正史、文人笔记、地方文献通盘考量,真正做到去伪存真;要对文献的历史背景、创作年代、作者职责、立场观点详加考定,并尽可能做出合理的最终判断,而不是沿袭古人的说法、照搬前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杜甫遗迹的历史变迁形成一个全面的认知过程。对夔州等变迁过程复杂,又因地质变迁而无法实地考察的遗迹,更要通过反复研读各类文献,探究其地理方位和变迁历程。
第三,注重文学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杨义认为:“探讨文学和地理的关系,他的本质意义在于……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怎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49]杜甫遗迹研究同样属于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通的过程,应当将杜甫遗迹放在杜甫本人、后世追慕者、遗迹探访者各自不同的时空去充分理解,展现其中的文化心态。例如,各地的杜甫墓之间历来便存在着真伪之争,每个杜甫墓的发展历程中都包含着与对手间的争讼。厘清现有文献,即可发现各地的历史依据均存在不足。在没有新出文献的前提下,真伪之争往往很难得出令所有人信服的结果。而研究历代寻访者、论证者、修建者的想法,不仅可以获知其中的文化心态,更能发掘杜甫墓中蕴含的对杜甫精神的追慕、崇祀、弘扬等深刻的文化意义。此外,注重运用传统沿革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对于探寻杜甫遗迹的本来面目与变迁历程大有裨益。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本书每一章篇名中对本地地名的称谓,均以此地杜甫遗迹出现时的地名为准。例如西安杜公祠的产生时间是明代,所以篇名中称“西安”而不用古称,这能够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杜甫遗迹真正出现的时间。
与此同时,本书写作也坚持了两个基本思路。
第一,突出问题意识,努力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重新审查前人的某些定论。杜甫及其相关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十分完备,所以,发现新问题一直是最大的难点。杜甫遗迹研究,实际上与杜甫接受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纳入杜甫接受研究的范畴。但需要指出的是,后人修建祠墓亭台纪念、祭祀杜甫,与文人在书斋中追慕杜甫往往在内容和内涵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杜甫形象的认知上。以西安、秦州、成州等地的杜公祠为例,历代重修过程中,杜甫的祭祀形象均不断发生变化。这是由各地修建遗迹的倡导者、组织者的多样化决定的。他们中不仅有为政一方的地方官员,还有倾慕杜甫的地方文人,甚至包括热爱地方文化的邑人乡绅和普通学子。这些人分属不同阶层,且并不都具有优秀文人的高雅意趣,因而其纪念、祭祀杜甫所怀的目的和诉求也会有所差异。特定时代、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对杜甫形象的认知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地方文化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的累加,使得杜甫遗迹所体现出的杜甫形象比文人书斋中的杜甫接受更加丰富,遗迹本身的文化内涵也更加多元且富有时代感。这不仅是前人没有关注过的新问题,也恰是研究杜甫遗迹的价值和趣味之一。此外,前人研究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误结论。例如鄜州羌村的具体地点,宋、明两代有不同说法,后人更是指出了两处具体所在。清人为调和矛盾,衍生出了杜甫在鄜州二次移家的说法,后渐为当今学者采纳。笔者经过充分考辨文献,得出了宋、明两说实为一处,杜甫在鄜州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
第二,充分尊重各地的地域文化精神。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各地杜甫遗迹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自唐以来,历史遗迹、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遗迹中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例如历史上出现过多处杜甫墓葬,本书研究了其中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这些墓葬之间必然存在真伪之争。但认为“假墓”毫无意义,仅有“真墓”才具备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不对的。每一处杜甫墓葬出现的缘由、发展的历程、保持至今的努力,都饱含着此地人对杜甫的追慕和地域文化对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接纳和弘扬。这些价值是超脱于真伪之外的,是杜甫遗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因此,笔者经过详细考辨认为,虽然四处杜甫墓在历史和文献依据上都并非完美,但应该充分尊重每一处杜甫墓的贡献和价值,视之为各地留给杜甫崇拜者和研究者的珍贵礼物。又如,当今研究已经证实,杜甫并未到过延州。若是单纯以历史学观点加以论证,延安的杜甫遗迹可以斥之为伪托、伪作,但如果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延安的杜甫遗迹同样是前代学者、官员敬仰杜甫、尊崇杜甫,并将杜甫视为与本地相关的名士,引为人生知己的产物。因此,尊重杜甫遗迹对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上述遗迹的解读也应该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心态,将杜甫遗迹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认知与体会。
[1]William Hung,TuFu:China's Grentest Poe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2;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文华:《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
[4]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霍松林:《杜甫与偃师》,《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
[6]魏泽一:《试论杜甫在湖南作诗的编次问题》,《文学遗产》1963年增刊第13辑。
[7]樊维纲:《杜甫湖南纪行诗编次诠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
[8]毛炳汉:《杜甫湖南诗新的总编次》,《文学遗产》1989年增刊总第18辑。
[9]文正义:《杜甫湘行踪迹及其死葬考》,《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2期。
[10]李一飞:《杜甫流寓湖南行事考辨三题》,《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
[11]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学术界》2016年第5期。
[12]丘良任:《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3]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14]师海军:《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
[15]聂大受:《杜甫陇右行迹及纪念物探赜(上、下)》,《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2013年第3期。
[16]洛阳师范学院、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主编:《洛阳明清碑志·偃师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7]刘雁翔:《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
[18]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9]吴敏霞主编:《长安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0]刘兆鹤、吴敏霞编著:《户县碑刻》,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21]李霞锋:《成都草堂古代碑刻初考》,《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
[22]郭世欣:《成都草堂遗址考》,《草堂》1981年第1期创刊号。
[23]王文才:《冀国夫人歌词及浣花亭考》,《草堂》1981年第2期。
[24]吴鼎南:《略谈古草堂、梵安两寺及杜甫草堂的位置》,《草堂》1981年第2期。
[25]周维扬:《从草堂唐碑出土略谈古今草堂寺之争》,《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26]陶喻之:《浣花古刹考略——唐益州正觉寺钩沉》,《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
[27]赵晓兰:《〈成都文类〉中的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28]刘洪:《再论浣花夫人、浣花祠与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
[29]杜甫纪念馆:《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草堂》1983年第1期。
[30]袁仁林:《杜甫寓夔故居考》,《草堂》1983年第1期。
[31]王大椿:《杜甫夔州高斋历代考察述评》,《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
[32]江均涛:《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草堂》1984年第1期。
[33]霍松林:《杜甫与偃师》,《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
[34]郑慧生:《杜氏家族与偃师杜甫墓地》,《寻根》2001年第5期。
[35]南新社等:《〈杜甫终葬巩县说〉质疑——与李丛昕先生商榷》,《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36]傅永魁:《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草堂》1982年第2期。
[37]李丛昕:《杜甫终葬巩县说——兼向霍松老请教》,《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38]刘玉珍:《诗圣杜甫和巩义杜甫墓》,《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39]张中一:《巩县与偃师杜甫墓辨析》,《草堂》1984年第1期。
[40]樊维纲:《杜甫后裔流域平江事考索》,《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41]董希如:《平江杜甫墓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0年第2期。
[42]吕兴才:《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3]刘雁翔:《杜甫陇上萍踪》,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4]蔡副全:《成县杜甫草堂历代诗碑考述》,《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
[45]蔡副全:《栗亭杜少陵祠考述》,《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46]周维扬、丁浩:《杜甫草堂史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47]邓荣生:《杜甫在平江》,黄河出版社2014年版。
[48]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
[49]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