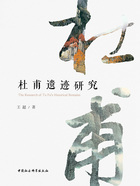
第一节 西安杜公祠与杜甫的祭祀形象
一 明代杜公祠的创建与乡贤杜甫
困守长安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但在长安为杜甫创建专祠已是七百余年后的明朝中后期。此时长安已改称西安,西安府下辖两个附郭县,东为咸宁县,西为长安县。
明嘉靖五年(1526),西安府学生员周鋐等人呈称,在咸宁县境内发现了杜甫墓。称杜甫“既卒,还葬长安。而今室莽莽然,垣隳而墟矣;墓累累然,木拱而薪矣!京兆弟子员吊孤远之躅,兴仰止之心,乃列牍请于巡抚中丞王荩”。经过巡抚陕西都察院都御史王荩等官员的讨论,决定“即其里,祠而祀之”[1],于咸宁县牛头寺勋荫坡新建杜公祠,命西安府知府赵伸主持兴建事宜[2]。杜甫遗迹的发现与杜子祠的创建又得到了西安本地文人的热情支持。西安府长安县人、原刑部主事张治道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3]。此前,他也曾参与到寻觅杜甫遗迹的活动之中,“余别业在韦、杜之间,因访杜曲有子美墓在焉,而其居为乡民牛氏宅,古迹虽存而表彰未行,遂请诸当道,为建一祠,以举祀事,时嘉靖丙戌春二月也”[4]。鉴于张治道的社会威望,杜公祠的创建工作亦由其具体负责。
但杜公祠建成未久,围绕着杜甫籍贯、建祠缘由等问题,就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执。创建杜公祠的碑文起初是由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浙江兰溪人唐龙撰写的。唐龙在《杜子祠记》开篇叙述道:“杜子,名甫,字子美,襄阳人也。……玄宗开元二十五年,预京兆荐贡而考功下之,困于长安之间。”唐龙作为外乡人,在杜甫籍贯问题上,按例遵照旧说,定籍襄阳,而长安仅为杜甫困寓之所。对于建祠缘由,唐龙则称:“子美岂特诗人已哉?夫子美乱不忘君,贫不苟禄,困不降志,盖有三难焉,……斯其难之至矣,则祠之也,固宜。况子美之诗,黜华挺实,削浮崇雅,畅叙彝伦,匡翼世教,风骚而下,无不愿执鞭焉。濯濯之灵,又何惭色于俎豆也?祀德者礼兴,甄烈者训广,诸君子于斯宏矣。”[5]由此可见,唐龙认为杜甫忠君爱国的品格、卓越不凡的诗才是建祠祭祀的依据所在,这与历来文人接受杜甫的主流观念相一致。
唐龙此文一出,即遭到以张治道为首的本地文人的激烈反对,对于杜甫身份认定的偏差,使得张治道深感杜子祠创建的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彰显,甚至为此耿耿于怀十余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张治道终于觅得良机,如愿在建祠十六年后重作《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文中对唐龙的不满溢于言表。张氏直言道:“诸公以余世家杜陵,且首倡祠事,命为之记,余辞,乃请诸提学副使唐龙为之刻矣。余以其文未详,实未当,而欲易之,未能也”,对当年谦辞撰写碑文一事颇为追悔。针对唐龙阐述的建祠原因,张治道指出:“自古道德文学风节之士,苟有关于世教者,建祠修祀,其道有三焉:曰生里,曰流寓,曰宦乡。生以表其灵,寓以彰其迹,宦以显其泽。有一于此,则建祠以祀。非其三者,虽贤弗祀。非弗祀也,无因也。”[6]毫不客气地否定了唐龙的建祠依据。
张治道考证认定杜甫“睿宗先天之二年生于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父(杜)闲徙杜陵生公,而少陵乃公故里。故公诗曰‘故里樊川曲’,而其迹不止于寓。上大礼、为拾遗,为率府胄曹、救房琯,而长安又其宦乡。故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生与寓与宦皆于其地,其祠而祀也,固宜”。强调长安为杜甫创建祠堂并非基于杜甫的道德文章,而是因为长安完全符合生里、流寓、宦乡三大条件。继而又因“邑里之前修之贤,埋灭弗闻,数百年来……竟无一宇一豆”[7],因此,为杜甫建祠实至名归。张治道的观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关中本地文人对于杜甫身份认知的代表观点。嘉靖二十一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亦将杜甫列为乡贤人物,其传记载:“杜甫,字子美,杜陵人。畿之后也。自杜预镇襄阳,子孙遂家焉。迄甫之父闲,生甫于杜陵。故甫有诗曰‘故里樊川曲’。”[8]
由此次争执可见,本地文人倡建杜公祠是为了祭祀作为“邑里前贤”的杜甫,重点在于“邑里”,至于杜甫的品格和诗才如何为人称颂,都只是杜甫成为“前贤”的依据罢了,抛开“邑里”,只说崇祀前贤是难以接受的。建祠理念冲突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地方文化需求。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配、影响之下,张治道的《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顺利取代了唐龙的《杜子祠记》,得以立石刻碑,留存至今。与此相同,这一观念也极为自然的融入地方志书的字里行间,明嘉靖《陕西通志》亦将杜甫列入《乡贤》之中。杜甫俨然被地方文人尊为本地乡贤的代表,杜公祠也成为地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
在杜公祠的创建过程中,也曾出现一些“杂音”。张治道在《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文末谈及时人对其热衷杜公祠创建一事的议论。“方余举杜祠时,仇者破其谋,谓当路曰‘为张子作行馆’。疾者阻其事,曰‘掘人坟墓’。后察其匪行罔掘,而督修益力,故不数月而告成。”[9]简而言之,人们对张治道的质疑,仅仅停留在张治道是否存在假公济私的可能,而当怀疑者发现张治道既没有把杜公祠当作自己的行馆,也没有破坏他人坟墓之后,议论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对于张治道创建杜公祠的深层次原因则未深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杜公祠的创建得到了当时广大官员、士人的一致赞同。
张治道逝世后,“缙绅大夫咸谓其薄仕进、耽风雅,与杜(甫)同,其里又同,宜并祀于祠,以彰德美”,遂“奉先生主于杜公之侧。事在己巳(明隆庆三年,1569)八月二十三日。维时里中父老儿童罔不欢忭,而缙绅大夫暨宗室之贤且文者、儒衣冠者,咸为诗文以纪其盛,大都谓杜公得先生为之继述,先生得杜公为之依归,称百世相感云”[10]。这也正是张治道的身后愿望,他在《遂谒杜工部祠》诗中云:“杜老诗名万古传,閟宫新造俯长川。村翁伏腊还今日,词客春游忆往年。俎豆神明严始祀,衣冠乡里慕前贤。往来韦杜城南胜,携手同歌尺五天。”[11]只有坐实杜甫的乡贤身份,这才有了张治道与杜甫携手同歌的可能性。在本地文士的推动下,张治道非常顺利的以乡贤身份配祀杜公祠,这不仅抬高张治道的地位,更进一步坐实了杜甫在关中文士心中的乡贤身份。
时至今日,杜甫出生地与葬地均不在长安,已为大多数学者认同。然而,明代以张治道为首的本地士人却坚持认为杜甫“生于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外来官员唐龙虽不在意杜甫的乡贤身份,却也认同杜甫“既卒,还葬长安”之说。这都表现了关中本地文人标举杜甫为乡贤的强烈愿望。但不论如何,祭祀杜甫而回避诗道及忠贞,只推乡贤,无疑是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祭祀活动是社会认知与民间接受的重要表现形式。“杜祠始建时,设春秋二祀”[12],香火鼎盛的乡贤形象与文人书斋里的杜甫形象相去甚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治道等人将杜甫列为乡贤,并极力与唐龙争辩的行为,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陕西关中地域文化兴盛,本地文士追溯先贤、传承地方文化的渴望。
二 清初重修杜公祠与诗圣杜甫
自明朝后期至清朝初年,关中地区迭遭灾祸,对关中文化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发生了关中大地震,关中文化精英马理、韩邦奇等人同日遇难,“号为极盛”的关中文风“自时厥后,此风遂衰”[13]。大地震带走了众多知名文士的同时,也给社会文化风气带来了重创。杜公祠每年春秋两次大规模祭祀“后以岁侵废秋”。为此,以王鹤为代表的关中士人虽极力奔走呼吁,甚至想借迎祀张治道入杜公祠的机会,再畅祭祀乡贤之风,“但两祀之缺一者,未能遂复耳”[14]。此时的杜甫依旧是乡贤,但杜公祠祭祀的社会影响却大不如前。
此后,明清易代,关中连年兵燹,给文化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杜公祠亦毁于延绵战火。入清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均经历了漫长的重建过程。清康熙六年(1667),咸宁县知县黄家鼎主持重修杜公祠,重修后的杜公祠远比明代规模宏大,但杜甫的身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当年的唐龙相似,黄家鼎也是外来官员。其在《重修杜公祠记》开篇就提出:“六经皆范世洪谟,而《诗》之为教,朴而易入,婉而多风,或出于忠臣孝子之心血,或出于劳人思妇之苦虑。感发善情,惩创逆意,甚盛典也。厥后,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歌行、乐府、五言、七言。唐遂以制科取士,故风雅一则独炽于唐。王、杨、卢、骆而后,踵接袂连,唯杜子美为最著”[15]。这一修祠的前提论断与张治道等人的理念完全不同。
黄家鼎提出重修杜公祠的理由有二:其一,“子美为诗,熟精《选》理,恺切达情。千余年来无不人愿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可见其重修杜公祠的首要因素就是从诗歌价值本身出发,祭祀作为诗圣的杜甫。其二,杜诗“揆之三百之旨、宣圣之论,其亦可以弗畔矣!……子美之学,孰非佐六经、裨世教之伟业也欤?顾安得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相承于弗替耶?”杜诗深蕴传统儒家教义,诗中体现了杜甫忠君爱国的国士情怀,理应得到后人崇祀。故此黄家鼎提出了“以子美之诗,求子美之学,法子美之忠孝、悱恻、和平、温厚,以鼓吹六经之教,为当世风范。谅不以此举为无功德之祀也”[16]。
黄氏心中值得祭祀的杜甫,是诗圣与国士身份合二为一的杜甫,而非其他。至于杜甫还是不是明朝人倡导了百年的西安乡贤,黄家鼎则毫不在意,只是说“余治之樊川,有子美祠……世久祠残”,于是结合上述两点理由,认为理应重修。当年作为乡贤配祀杜公祠的张治道,黄氏则根本不予提及,只说“余趋拜于兹,读太微碑于蔓草间。载始末最详”[17]。
重修杜公祠后,明末遗民、位列“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曾游览新祠,并赋诗一首:“城南韦杜潏川滨,工部千秋庙貌新。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陂前鸟弄春。稷契平生空自许,谁知词客有经纶。”[18]诗中体现出的杜甫的认识与黄家鼎完全契合。杜公祠在排斥外来论调百年后,终归在这次由外乡人倡导的重修中磨去了原有的地域文化烙印。
易代之后,杜甫乡贤身份隐去,诗圣身份重显,这一变迁历程绝非源自黄家鼎的个人好恶,而是缘于地域文化氛围的改变。黄家鼎曾于杜公祠颓壁间,见本地文人陈大经所题绝句:“诗意逐处染江烟,故里谁曾识象贤?冷落檐牙风雨里,几声啼鸟可人怜。”[19]乡贤久已无人祭祀,效法先人之贤德更是无从谈起。此情此景,足见入清后的世情变化与杜公祠寂寥之貌。
重修杜公祠既由官府主导,本地文士、邑人参与无多,或许加速了杜公祠的衰败。三十余年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陕西巡抚鄂海之子、满洲人达礼善随父客居西安府,“尝按图考书,知咸宁城南有杜工部祠”,前往探访,见杜公祠荒废破败,遂捐资重修。达礼善作为满洲后裔,对中原文明素怀仰慕之心,自称“素嗜杜诗,吟咏之下,尝慨杜公所遭不偶。即其诗以相见其人,即其人以三复其诗。窃讶唐以诗取士,而公反不与制科之选,未尝不三致意焉”[20],故见杜公祠荒废,心生不忍。达理善对杜公祠的创建经过并不了解也并不在意,称“其祠创自有明咸宁令张君”,这显然是误将张治道当作嘉靖年间的咸宁县知县了。至此,杜甫的诗圣身份认定以及杜公祠的祭祀内涵与明人倡导的乡贤身份彻底脱节,杜公祠祭祀活动也由众多关中文士、广大社会民众广泛参与,演变成了为政一方、倾慕杜甫的地方官员及外来文人的小规模自发行为。
三 清中期重修杜公祠与乡贤杜甫的回归
随着清朝统治秩序的巩固,社会生活逐步安定,关中文化也渐有复兴之势。与此相应,乾隆初年,关中文人及乡里有感于杜公祠破败,拟捐资重修。求学于关中书院的同州府大荔县人李法作《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与康熙年间两次重修不同,李法重提了杜甫宗族世系及“杜曲故里”说:“韦曲绕皇子陂而东一带,崖赤如日,曰少陵原。唐工部杜子美之所以得号也。原麓一溪东来,水田如绣,水曲有村,曰杜曲。公家十一宰相,及诸贵所生处,是则公里矣。而世传公生于襄城,或亦有据,然贯仍杜,而家仍杜也。”这继承了明代张治道的“邑里前贤”说,为修祠重添了崇祀乡贤的色彩。更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修祠的提议者是“公里长者”,乡里社会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数十年无人提及的张治道在文中被反复提及,且张氏后人也在重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工程竣工后,为解决杜公祠平日养护、祭祀所需,特置“祠地若干,求(杜)公裔莳艺,及张裔视祀伏腊忌,且时补葺之,致勿颓”[21]。乾隆年间,随着杜公祠的新修,杜甫与张治道的长安乡贤身份重新得到乡里社会的认同及重视,这与关中地域文化的逐步复兴密切相关。
此次虽然重提祭祀乡贤的理念,但士人与乡里并不排斥其他祭祀内涵的存在。主持重修的官员认为杜甫之“诗歌与身所行事无一不可为后人师。唐无儒,于盛唐,其最(杜)公矣!张(治道)亦偃蹇不显官,挟持遭遇,为杜具体。非徒文章德谊抗一世。乡先生殁,而祭于社,永风教也”[22]。李法等本地士人对此并无异议。由此可见,杜甫乡贤身份的复归与诗圣、国士身份没有发生主次之争,反而形成了乡贤与诗圣、国士三位一体的格局,关中地域文化在本位与兼容之间取得了相对的平衡,并持续百年。嘉庆年间杜公祠虽曾遭遇火灾,但旋即由“邑士人杨调鼎、王淳敬等请于巡抚方公维甸捐资改建于牛头寺东……神像配像如旧制”[23],与乾隆时并无二致。
四 清末社会动荡与国士杜甫
宋代以后,大抵每逢民族矛盾激化、战乱频仍之时,文人、士大夫都会在山河破败的寂寥感中读杜诗,追缅杜甫忠君爱国的“国士”之心。清咸丰后期至同治年间,社会日益动荡,南有太平天国起义,而地处北方的关中地区则饱受“回乱”及捻军的冲击,杜公祠也在战乱中再度颓毁。同治七年(1868),关中地区平定不久,陕西布政使、福建人林寿图捐资重修杜公祠,由其门客、内阁中书谢章铤撰《重修杜工部祠碑》。碑记虽沿袭“工部虽籍襄阳而实出长安之杜”的故里说,但后文却着重追述了布政使林寿图坐镇关中、平定战乱的过程中,“一灯独照,念子美许身稷契之言”,与杜甫忠君爱国思想发生共鸣,深为感慨地说:“嗟乎!唐人之诗多矣,而李杜独尊,往往尸祝者,何哉?岂真有私于其乡先生耶?毋亦以其能轻富贵,不敢以无赖及国家也。不然,子美始善房琯,继善严武,稍为委蛇,皆足以取世资,乃何以每饭不忘君如此,而老大意拙又若彼也”[24]。明确指出后人祭祀杜甫绝非因其为乡贤,也并非因其诗文成就无人可及,而是因其每饭不忘君恩、终身忠贞爱国的气节操守,足以赢得后人以国士尊之、敬之并祭祀之。
伴随着战乱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凋零,乡里文化再度落潮。杜公祠的祭祀再次失去了社会响应,完全回到了士人和少数文人的小圈子中。与此前一般,缺乏乡里邑人的维持,祠宇很快破败如故。
光绪十三年(1887),陕西巡抚、安徽人叶伯英与同僚再度捐资重修杜公祠。叶伯英撰《重修杜工部祠堂记》曰:“杜工部子美者,绍承家学,其诗宗三百篇及楚骚、汉魏乐府。故气格苍古,酝酿深醇,卓然为有唐之冠。元稹谓为集诗家之大成,洵千古定评也。然公不仅以诗鸣也,以一小臣旋遭罢黜,困苦艰难,流寓于成都、同谷、羌村之地,而独忧时感事,每饭不忘朝廷。噫!非一片忠爱出于天性者,能如斯之惓惓乎?而可弗祀乎?”[25]阐明其倡导重修不仅是推崇杜诗,更是为了追慕杜甫忠君爱国之心。继而感慨“公(杜甫)之才能抗太白而不能举进士,身能比稷契而不能逢尧舜。谟议能结元宗(玄宗)之知,致严武之荐,而不能免妻子之冻馁,弭骨月(肉)之流离。……后之诵公诗、谒公祠者,当悯公之遭,知公之志,勿等忧危于讦激,视忠爱为刺讥也”。这既是对杜甫不幸遭遇的悲悯,也是由时局而生的共鸣。可见叶氏心中真正祭祀着的恰是一腔忠爱的国士杜甫。此后直至民国,杜公祠虽又历数次修葺,但其祭祀文化内涵再未演变。